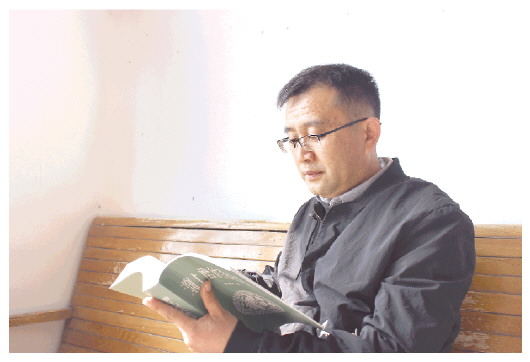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天空de童话
近日,记者在安丘市大盛镇牛沐村见到了潍坊历史文化学者牛鹏志。担任安丘市教体局驻牛沐村第一书记多年,牛鹏志淬炼出独特的治学范式,既能在故纸残卷中辨章学术,又能从耄耋乡贤口述间考镜源流,这种“接地气”的治学方式,铸就他笔下鲜活的历史图景。
□文/图 本报记者 王鲁萍
做潍坊文史的“慢耕者”
如同撑篙的寻梦者,在潍坊历史文化的长河里漫溯,向着青草更青处探寻。2010年是牛鹏志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将研究视野转向潍坊地域文史领域,确立了古典诗词与古籍文献两大研究方向。
研究初期,牛鹏志像寻宝者般穿梭于各县市的地方诗集中。《东武诗存》《营陵诗略》《益都先正诗丛钞》等古代诗歌总集成为案头常客。2011年春,当《渠风集略》《渠风续集》《潍诗采录》的纸页在牛鹏志手中展开时,那些泛黄纸张里的墨痕如地质断层般显影出文化沉积层,其间蛰伏的文明矿脉正等待他挖掘。他以此为起点,深耕细作,此后又逐渐扩展到潍坊各个县市区的文史领域研究。
2013年牛鹏志参与《安丘历史文化丛书》编纂时,与曹昭民合作完成《渠风流韵》。这部收录古今千余首安丘诗词作品的选集,不仅是对安丘诗脉的系统梳理,更成为他后续研究的基石。同期启动的《潍上古诗词》因工程浩大,让他真正体会到“上下求索”的艰辛。为搜集散落全国的340余位诗人、2000多首诗词,四年间,他和合作者王新的足迹遍布国内各个大型图书馆。
学术研究需要“慢功夫”
当大众通过短视频获取历史知识时,研究者的使命就是为其提供经过严谨考证的“原料”。“专业研究者研究了多年的结论,会让大众短时间内正确了解,并引发关注,而这正是我们文史研究者的价值所在。”牛鹏志说。
《安丘历代著述考》《潍上历代著述考》是牛鹏志“文火慢炖”的结晶。这两部书都是牛鹏志从2012年开始撰写,《安丘历代著述考》耗其8年心血,梳理出安丘344位先贤的972种古代著述;《潍上历代著述考》历时10年完成,收录370余位作者的千种著述。
这些看似枯燥的文献考据工作,让牛鹏志深切感受到潍坊文化的“充实而有光辉”。牛鹏志说:“我常常被我们潍坊历史文化的深厚华美、博大壮阔所震撼。按照古人的笺注,‘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我们潍坊的历史文化就是有这样一种‘大美’的魅力。”
在历史断裂处续接文脉
谈及治学理念,牛鹏志尤为推崇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学术洞见,主张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当以深掘地域文化矿脉为根基,构建世界文明坐标系为视野。
牛鹏志认为,这种古今贯通、各领域互联的全局视野,在近年研究中愈发重要。“当我们将清代潍坊诗人齐培元的《雁字诗》置于艺术史维度审视,就能发现其‘点衬残星横汉北,钩连新月照天南’不仅是诗句,更是书画创作的经验凝练。”牛鹏志说,这种诗书画互通的案例,正提示我们要打破学科壁垒——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不能画地为牢,而应成为联通文学、艺术、民俗等各领域的桥梁。牛鹏志鼓励当代的青年学者,一定要敢于挑战,敢于做大事和难事,要有一种“补天裂”的豪情和使命。
“如果为百年后的研究者埋下一枚‘时间胶囊’,您会选择放入哪件最具潍坊文化特质的物品?”面对记者的提问,牛鹏志答:“我会选择《潍坊古籍佚失名录》,因为整个潍坊地区古籍文献,有三分之二现在都已经佚失,它既是我们这代人的遗憾清单,更是留给未来的寻宝图。”于时光的尘埃中打捞文明,在历史的断裂处续接文脉,这种期待正是支撑无数潍坊历史文化研究者继续前行的力量。
□文/图 本报记者 王鲁萍
做潍坊文史的“慢耕者”
如同撑篙的寻梦者,在潍坊历史文化的长河里漫溯,向着青草更青处探寻。2010年是牛鹏志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将研究视野转向潍坊地域文史领域,确立了古典诗词与古籍文献两大研究方向。
研究初期,牛鹏志像寻宝者般穿梭于各县市的地方诗集中。《东武诗存》《营陵诗略》《益都先正诗丛钞》等古代诗歌总集成为案头常客。2011年春,当《渠风集略》《渠风续集》《潍诗采录》的纸页在牛鹏志手中展开时,那些泛黄纸张里的墨痕如地质断层般显影出文化沉积层,其间蛰伏的文明矿脉正等待他挖掘。他以此为起点,深耕细作,此后又逐渐扩展到潍坊各个县市区的文史领域研究。
2013年牛鹏志参与《安丘历史文化丛书》编纂时,与曹昭民合作完成《渠风流韵》。这部收录古今千余首安丘诗词作品的选集,不仅是对安丘诗脉的系统梳理,更成为他后续研究的基石。同期启动的《潍上古诗词》因工程浩大,让他真正体会到“上下求索”的艰辛。为搜集散落全国的340余位诗人、2000多首诗词,四年间,他和合作者王新的足迹遍布国内各个大型图书馆。
学术研究需要“慢功夫”
当大众通过短视频获取历史知识时,研究者的使命就是为其提供经过严谨考证的“原料”。“专业研究者研究了多年的结论,会让大众短时间内正确了解,并引发关注,而这正是我们文史研究者的价值所在。”牛鹏志说。
《安丘历代著述考》《潍上历代著述考》是牛鹏志“文火慢炖”的结晶。这两部书都是牛鹏志从2012年开始撰写,《安丘历代著述考》耗其8年心血,梳理出安丘344位先贤的972种古代著述;《潍上历代著述考》历时10年完成,收录370余位作者的千种著述。
这些看似枯燥的文献考据工作,让牛鹏志深切感受到潍坊文化的“充实而有光辉”。牛鹏志说:“我常常被我们潍坊历史文化的深厚华美、博大壮阔所震撼。按照古人的笺注,‘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我们潍坊的历史文化就是有这样一种‘大美’的魅力。”
在历史断裂处续接文脉
谈及治学理念,牛鹏志尤为推崇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学术洞见,主张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当以深掘地域文化矿脉为根基,构建世界文明坐标系为视野。
牛鹏志认为,这种古今贯通、各领域互联的全局视野,在近年研究中愈发重要。“当我们将清代潍坊诗人齐培元的《雁字诗》置于艺术史维度审视,就能发现其‘点衬残星横汉北,钩连新月照天南’不仅是诗句,更是书画创作的经验凝练。”牛鹏志说,这种诗书画互通的案例,正提示我们要打破学科壁垒——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不能画地为牢,而应成为联通文学、艺术、民俗等各领域的桥梁。牛鹏志鼓励当代的青年学者,一定要敢于挑战,敢于做大事和难事,要有一种“补天裂”的豪情和使命。
“如果为百年后的研究者埋下一枚‘时间胶囊’,您会选择放入哪件最具潍坊文化特质的物品?”面对记者的提问,牛鹏志答:“我会选择《潍坊古籍佚失名录》,因为整个潍坊地区古籍文献,有三分之二现在都已经佚失,它既是我们这代人的遗憾清单,更是留给未来的寻宝图。”于时光的尘埃中打捞文明,在历史的断裂处续接文脉,这种期待正是支撑无数潍坊历史文化研究者继续前行的力量。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05/Page05-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06/Page06-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07/Page07-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08/Page08-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09/Page09-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10/Page10-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11/Page11-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12/Page12-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13/Page13-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14/Page14-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15/Page15-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415/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