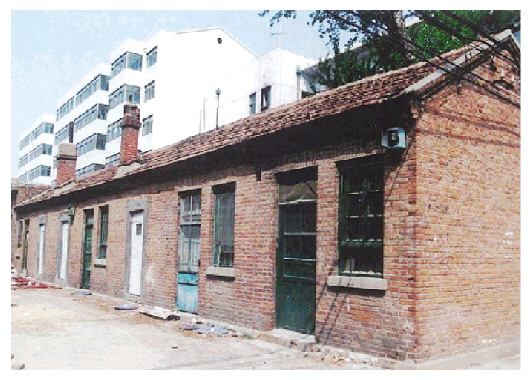04版:拥抱2024
04版:拥抱2024
- * “18个针眼”实现人生价值
- * 帮扶的孩子们越来越好
- * 晚报助我圆了大学梦
- * 画展上开生日会好难忘
 05版:拥抱2024
05版:拥抱2024
- * 用音乐奏响更美的旋律
- * 期待巴黎奥运会再突破
- * 创作更好作品致敬家乡
- * 继续去各个村里放电影
 10版:拥抱2024 我们30岁了之成长见证
10版:拥抱2024 我们30岁了之成长见证
- * 与潍县战役亲历者对话
- * 沂山之巅寻迹齐长城
- * 旅程有尽头 友谊无终点
 14版:拥抱2024 我们30岁了之晚报情缘
14版:拥抱2024 我们30岁了之晚报情缘
- * 一场奇妙的遇见
- * “人文”情缘亦师亦友
- * 如果你拍冬天 就不能只拍冬天
- * 此心安处是吾乡
 16版:拥抱2024 我们30岁了
16版:拥抱2024 我们30岁了
- * 一起再出发
逄春阶
《潍坊晚报》走过了三十年的匆匆岁月,她见证了潍坊的巨大变迁,滋润了风筝都老百姓的心田。作为参与了她创刊的报人,我由衷地祝福她。前几天,没见面的新同事让我回忆一下创刊的一些细节。鲜活的细节真是不少,一时无从下笔。我珍藏着《潍坊晚报》创刊号,也写过创刊前后的日记,可惜一时找不到。就凭记忆说几件事吧。
从1992年起,我在潍坊日报文体部当“周末版”的二版编辑,编辑部设在当时的工农路41号。那时,我27岁,一门心思地组稿、编稿、画版、校对,干得很带劲儿。那是我成为报人的起点。
1993年春天,我们部门开业务例会,王存玉主任好像那天有事,主持工作的胡全福副主任说潍坊日报社筹备创刊《潍坊晚报》,孔德平老师去干副刊部主任,他推荐我干文学副刊编辑。我非常高兴,平时我就爱缠着孔老师讲诗歌,这下更方便了。当天晚上,文体部的同事们给我们送别,那天不知怎么竟然喝醉了,是因为对老同事的留恋,还是对新岗位的憧憬?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吐得一塌糊涂,趴在编辑部的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天色已黑,同事们都走了,王存玉主任还没走,递给我一杯水,说:“去了晚报好好干,做一个真正的报人,你写的稿子,哪怕有一句让人记住,也就有了价值。怎么才能让人记住?要有骨气,说真话,说人话。”王主任的话,我一开始觉得也就是大白话,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他说的,要做到非常不容易,但却是一个报人应该做的。
从各个部门抽调的人集中起来,编辑部设在原潍坊市地震局院内。可是《潍坊晚报》创刊遇到了麻烦,刊号迟迟批不下来,人员都组织起来了,又不好解散,大家都各自找事干。我记得广告公司有一阵还办了一个音乐蜡烛厂,我也帮着推销过蜡烛。
孔德平老师嘱咐我,无法办报,正好可以充充电。他给了我一本孔孚先生的诗论集《远龙之扪》,有近20万字吧。我看了一遍,觉得不过瘾,又用窗户纸订成的本子抄了一遍,大概花了一个月时间。一字一句地抄,一字一句地琢磨,慢慢地,才对什么是好诗有了更深的理解,觉得忽然开了窍。
参与创刊的大都是年轻人,坐不住。转眼到了夏天,刊号还没批下来,总编辑张世新联系了淄博晚报,让我们年轻人去学习,张总让我领队。我从小到大就没当过干部,突然叫我领着四个同事去淄博,一时没有头绪。临别,张总嘱咐我,千万别出事,尤其不能出安全事故,平时跟着淄博晚报的人实习,回到宾馆就不要乱动了,出门要请假。我当时太死板了,管理得太死,就连人家上街买个牙膏也要管。有一天,淄博晚报组织我们去蒲松龄故居参观,我们拜谒了蒲松龄搜集故事的柳泉、蒲松龄墓等地,我还买了一把南泥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有人提出找个小酒馆喝点酒,我其实也想喝,但想起张总的嘱咐,就没松口,几个同事闷闷不乐地到食堂里各自吃饭。
我们一起住在淄博晚报社大厦边上的一个宾馆里,我跟王志刚一个房间,吃完饭就在宾馆里看书,一直看到夜里10点。刚灭了灯,我正跟王志刚聊天呢,聊的是蒲松龄的鬼故事,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起身去开门,门刚打开一条缝,一个披头散发的“鬼”就“嗷”的一声,后面还站着两个,也是披头散发,张着大红嘴巴,我顺手抄起了屋里的扫帚,从里边伸出来,闭着眼睛一个劲儿地打,然后嘴里嚷嚷着:“鬼,女鬼……”王志刚爬起来,问:“在哪里,在哪里?”就听门外哈哈大笑。原来是三个美女同事捣鬼,她们当时也就二十一二岁,刚刚大学毕业,正是顽皮的时候,她们把脸用化妆品化成鬼模样,头发披散着,身上披着被单子。见我吓成那副鬼样子,不知道她们中的谁开口了:“小逄你也知道害怕啊?我们还以为你是木头人,除了工作啥也不知道呢。”我的脸一下子火烧一般,这才明白自己简单僵化的管理方式伤害了大家,她们这是在抗议呢。
半夜惊魂,给不苟言笑的我上了一课。
之后,我的心态也慢慢放松了,让大家各自安排时间。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玩的时候玩。有时,我们也去小店里小酌,吹吹牛。我们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跟淄博晚报的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朋友直到现在还交往,比如郝永勃,他成了我省的知名作家。
1993年底,试刊了两期后,刊号终于批下来,1994年1月1日正式创刊。1日下午,散发着油墨香的《潍坊晚报》印出来了,我们都到街上去卖,市民纷纷驻足,有的人一下子买了20份,说是要收藏。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报纸一直卖到晚上8点多,张总说,大家庆贺一下,都喝了点酒。
创刊了,日子一下紧张起来。孔德平老师特别信任我,他把一摞空白签稿单给我,在主任签字一栏全部写上“孔”字,也就是说,只要通过我审核的稿子,可以直接上版。孔老师提前签好了字,是彻底放权,他这样,我反而更紧张、更认真地编稿。
1995年的秋天,我又接到去安丘王家庄子扶贫的任务,离开了编辑部,住在峡山水库边上的东吴家漫村,但我依然给《潍坊晚报》写稿子。1996年9月,我开始在大众日报驻潍坊记者站试用写稿,不久成了驻站记者,1999年7月调到了济南。
在晚报的日子,是我在潍坊最难忘的日子,同事之间互相照顾,真是亲如兄弟姐妹,业务氛围很浓厚,有时为了一个新闻标题争论不休。我记得,有一次张总不同意刊发一篇稿子,批了一段话,李学敏主任在张总批示的上面写了一段话,给张总“批示”回去,据理力争,稿子终于上了版。有的稿子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见报,记者想不通,主任就请记者到小店吃饭、喝酒,泄泄火。等记者消了气,第二天又奔跑在大街小巷。想起我的那些可爱的同事们,心里就很温暖,眼窝发湿。
大家不光在办报上互相关心,生活上也互相关心。我记得1994年秋天,我三舅开着拖拉机从安丘景芝镇到潍坊城区卖鲜玉米,一天没卖出几斤,他很沮丧地开着拖拉机找到我。孔老师就跟同事们说,小逄的舅舅不容易,大家帮帮忙,咱把这车鲜玉米买下来吧。鲜玉米卸在编辑部旁边的空地上,我三舅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这样感人的细节还有很多。
整天在全国各地采访,我回老家的日子越来越少。有时到潍坊出差,在宾馆的大厅里看到报夹,我会拿起《潍坊晚报》找我熟悉的同事,找到一个名字,就像见到了宝贝一样。后来,我的同事大多退休,或者担任了报社领导,不再在一线写稿子了,但我依然会从头版翻到末版,在内心里,我一直觉得我是“晚报的人”。
别人无法理解我的心情,《潍坊晚报》是一份我曾经见证她诞生的报纸啊,她的版面上曾经有我的痕迹。说真话,虽然离开了,但我依然牵挂她。
《潍坊晚报》走过了三十年的匆匆岁月,她见证了潍坊的巨大变迁,滋润了风筝都老百姓的心田。作为参与了她创刊的报人,我由衷地祝福她。前几天,没见面的新同事让我回忆一下创刊的一些细节。鲜活的细节真是不少,一时无从下笔。我珍藏着《潍坊晚报》创刊号,也写过创刊前后的日记,可惜一时找不到。就凭记忆说几件事吧。
从1992年起,我在潍坊日报文体部当“周末版”的二版编辑,编辑部设在当时的工农路41号。那时,我27岁,一门心思地组稿、编稿、画版、校对,干得很带劲儿。那是我成为报人的起点。
1993年春天,我们部门开业务例会,王存玉主任好像那天有事,主持工作的胡全福副主任说潍坊日报社筹备创刊《潍坊晚报》,孔德平老师去干副刊部主任,他推荐我干文学副刊编辑。我非常高兴,平时我就爱缠着孔老师讲诗歌,这下更方便了。当天晚上,文体部的同事们给我们送别,那天不知怎么竟然喝醉了,是因为对老同事的留恋,还是对新岗位的憧憬?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吐得一塌糊涂,趴在编辑部的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天色已黑,同事们都走了,王存玉主任还没走,递给我一杯水,说:“去了晚报好好干,做一个真正的报人,你写的稿子,哪怕有一句让人记住,也就有了价值。怎么才能让人记住?要有骨气,说真话,说人话。”王主任的话,我一开始觉得也就是大白话,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他说的,要做到非常不容易,但却是一个报人应该做的。
从各个部门抽调的人集中起来,编辑部设在原潍坊市地震局院内。可是《潍坊晚报》创刊遇到了麻烦,刊号迟迟批不下来,人员都组织起来了,又不好解散,大家都各自找事干。我记得广告公司有一阵还办了一个音乐蜡烛厂,我也帮着推销过蜡烛。
孔德平老师嘱咐我,无法办报,正好可以充充电。他给了我一本孔孚先生的诗论集《远龙之扪》,有近20万字吧。我看了一遍,觉得不过瘾,又用窗户纸订成的本子抄了一遍,大概花了一个月时间。一字一句地抄,一字一句地琢磨,慢慢地,才对什么是好诗有了更深的理解,觉得忽然开了窍。
参与创刊的大都是年轻人,坐不住。转眼到了夏天,刊号还没批下来,总编辑张世新联系了淄博晚报,让我们年轻人去学习,张总让我领队。我从小到大就没当过干部,突然叫我领着四个同事去淄博,一时没有头绪。临别,张总嘱咐我,千万别出事,尤其不能出安全事故,平时跟着淄博晚报的人实习,回到宾馆就不要乱动了,出门要请假。我当时太死板了,管理得太死,就连人家上街买个牙膏也要管。有一天,淄博晚报组织我们去蒲松龄故居参观,我们拜谒了蒲松龄搜集故事的柳泉、蒲松龄墓等地,我还买了一把南泥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有人提出找个小酒馆喝点酒,我其实也想喝,但想起张总的嘱咐,就没松口,几个同事闷闷不乐地到食堂里各自吃饭。
我们一起住在淄博晚报社大厦边上的一个宾馆里,我跟王志刚一个房间,吃完饭就在宾馆里看书,一直看到夜里10点。刚灭了灯,我正跟王志刚聊天呢,聊的是蒲松龄的鬼故事,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起身去开门,门刚打开一条缝,一个披头散发的“鬼”就“嗷”的一声,后面还站着两个,也是披头散发,张着大红嘴巴,我顺手抄起了屋里的扫帚,从里边伸出来,闭着眼睛一个劲儿地打,然后嘴里嚷嚷着:“鬼,女鬼……”王志刚爬起来,问:“在哪里,在哪里?”就听门外哈哈大笑。原来是三个美女同事捣鬼,她们当时也就二十一二岁,刚刚大学毕业,正是顽皮的时候,她们把脸用化妆品化成鬼模样,头发披散着,身上披着被单子。见我吓成那副鬼样子,不知道她们中的谁开口了:“小逄你也知道害怕啊?我们还以为你是木头人,除了工作啥也不知道呢。”我的脸一下子火烧一般,这才明白自己简单僵化的管理方式伤害了大家,她们这是在抗议呢。
半夜惊魂,给不苟言笑的我上了一课。
之后,我的心态也慢慢放松了,让大家各自安排时间。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玩的时候玩。有时,我们也去小店里小酌,吹吹牛。我们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跟淄博晚报的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朋友直到现在还交往,比如郝永勃,他成了我省的知名作家。
1993年底,试刊了两期后,刊号终于批下来,1994年1月1日正式创刊。1日下午,散发着油墨香的《潍坊晚报》印出来了,我们都到街上去卖,市民纷纷驻足,有的人一下子买了20份,说是要收藏。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报纸一直卖到晚上8点多,张总说,大家庆贺一下,都喝了点酒。
创刊了,日子一下紧张起来。孔德平老师特别信任我,他把一摞空白签稿单给我,在主任签字一栏全部写上“孔”字,也就是说,只要通过我审核的稿子,可以直接上版。孔老师提前签好了字,是彻底放权,他这样,我反而更紧张、更认真地编稿。
1995年的秋天,我又接到去安丘王家庄子扶贫的任务,离开了编辑部,住在峡山水库边上的东吴家漫村,但我依然给《潍坊晚报》写稿子。1996年9月,我开始在大众日报驻潍坊记者站试用写稿,不久成了驻站记者,1999年7月调到了济南。
在晚报的日子,是我在潍坊最难忘的日子,同事之间互相照顾,真是亲如兄弟姐妹,业务氛围很浓厚,有时为了一个新闻标题争论不休。我记得,有一次张总不同意刊发一篇稿子,批了一段话,李学敏主任在张总批示的上面写了一段话,给张总“批示”回去,据理力争,稿子终于上了版。有的稿子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见报,记者想不通,主任就请记者到小店吃饭、喝酒,泄泄火。等记者消了气,第二天又奔跑在大街小巷。想起我的那些可爱的同事们,心里就很温暖,眼窝发湿。
大家不光在办报上互相关心,生活上也互相关心。我记得1994年秋天,我三舅开着拖拉机从安丘景芝镇到潍坊城区卖鲜玉米,一天没卖出几斤,他很沮丧地开着拖拉机找到我。孔老师就跟同事们说,小逄的舅舅不容易,大家帮帮忙,咱把这车鲜玉米买下来吧。鲜玉米卸在编辑部旁边的空地上,我三舅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这样感人的细节还有很多。
整天在全国各地采访,我回老家的日子越来越少。有时到潍坊出差,在宾馆的大厅里看到报夹,我会拿起《潍坊晚报》找我熟悉的同事,找到一个名字,就像见到了宝贝一样。后来,我的同事大多退休,或者担任了报社领导,不再在一线写稿子了,但我依然会从头版翻到末版,在内心里,我一直觉得我是“晚报的人”。
别人无法理解我的心情,《潍坊晚报》是一份我曾经见证她诞生的报纸啊,她的版面上曾经有我的痕迹。说真话,虽然离开了,但我依然牵挂她。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07/Page07-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08/Page08-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09/Page09-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10/Page10-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11/Page11-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12/Page12-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13/Page13-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14/Page14-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15/Page15-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01/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