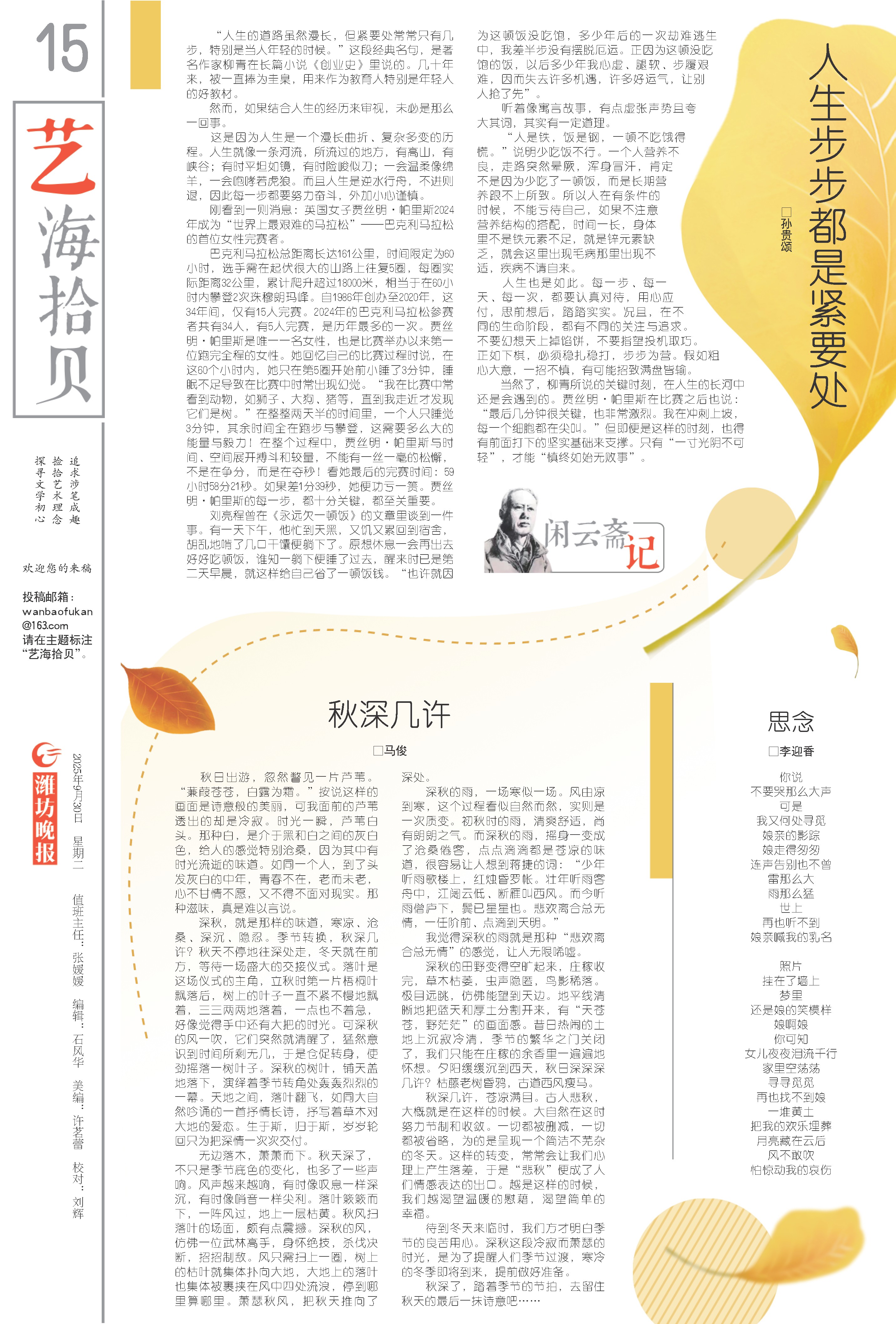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大地的色彩
□马俊
秋日出游,忽然瞥见一片芦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按说这样的画面是诗意般的美丽,可我面前的芦苇透出的却是冷寂。时光一瞬,芦苇白头。那种白,是介于黑和白之间的灰白色,给人的感觉特别沧桑,因为其中有时光流逝的味道。如同一个人,到了头发灰白的中年,青春不在,老而未老,心不甘情不愿,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那种滋味,真是难以言说。
深秋,就是那样的味道,寒凉、沧桑、深沉、隐忍。季节转换,秋深几许?秋天不停地往深处走,冬天就在前方,等待一场盛大的交接仪式。落叶是这场仪式的主角,立秋时第一片梧桐叶飘落后,树上的叶子一直不紧不慢地飘着,三三两两地落着,一点也不着急,好像觉得手中还有大把的时光。可深秋的风一吹,它们突然就清醒了,猛然意识到时间所剩无几,于是仓促转身,使劲摇落一树叶子。深秋的树叶,铺天盖地落下,演绎着季节转角处轰轰烈烈的一幕。天地之间,落叶翻飞,如同大自然吟诵的一首抒情长诗,抒写着草木对大地的爱恋。生于斯,归于斯,岁岁轮回只为把深情一次次交付。
无边落木,萧萧而下。秋天深了,不只是季节底色的变化,也多了一些声响。风声越来越响,有时像叹息一样深沉,有时像哨音一样尖利。落叶簌簌而下,一阵风过,地上一层枯黄。秋风扫落叶的场面,颇有点震撼。深秋的风,仿佛一位武林高手,身怀绝技,杀伐决断,招招制敌。风只需扫上一圈,树上的枯叶就集体扑向大地,大地上的落叶也集体被裹挟在风中四处流浪,停到哪里算哪里。萧瑟秋风,把秋天推向了深处。
深秋的雨,一场寒似一场。风由凉到寒,这个过程看似自然而然,实则是一次质变。初秋时的雨,清爽舒适,尚有朗朗之气。而深秋的雨,摇身一变成了沧桑倦客,点点滴滴都是苍凉的味道,很容易让人想到蒋捷的词:“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我觉得深秋的雨就是那种“悲欢离合总无情”的感觉,让人无限唏嘘。
深秋的田野变得空旷起来,庄稼收完,草木枯萎,虫声隐匿,鸟影稀落。极目远眺,仿佛能望到天边。地平线清晰地把蓝天和厚土分割开来,有“天苍苍,野茫茫”的画面感。昔日热闹的土地上沉寂冷清,季节的繁华之门关闭了,我们只能在庄稼的余香里一遍遍地怀想。夕阳缓缓沉到西天,秋日深深深几许?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
秋深几许,苍凉满目。古人悲秋,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大自然在这时努力节制和收敛。一切都被删减,一切都被省略,为的是呈现一个简洁不芜杂的冬天。这样的转变,常常会让我们心理上产生落差,于是“悲秋”便成了人们情感表达的出口。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渴望温暖的慰藉,渴望简单的幸福。
待到冬天来临时,我们方才明白季节的良苦用心。深秋这段冷寂而萧瑟的时光,是为了提醒人们季节过渡,寒冷的冬季即将到来,提前做好准备。
秋深了,踏着季节的节拍,去留住秋天的最后一抹诗意吧……
秋日出游,忽然瞥见一片芦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按说这样的画面是诗意般的美丽,可我面前的芦苇透出的却是冷寂。时光一瞬,芦苇白头。那种白,是介于黑和白之间的灰白色,给人的感觉特别沧桑,因为其中有时光流逝的味道。如同一个人,到了头发灰白的中年,青春不在,老而未老,心不甘情不愿,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那种滋味,真是难以言说。
深秋,就是那样的味道,寒凉、沧桑、深沉、隐忍。季节转换,秋深几许?秋天不停地往深处走,冬天就在前方,等待一场盛大的交接仪式。落叶是这场仪式的主角,立秋时第一片梧桐叶飘落后,树上的叶子一直不紧不慢地飘着,三三两两地落着,一点也不着急,好像觉得手中还有大把的时光。可深秋的风一吹,它们突然就清醒了,猛然意识到时间所剩无几,于是仓促转身,使劲摇落一树叶子。深秋的树叶,铺天盖地落下,演绎着季节转角处轰轰烈烈的一幕。天地之间,落叶翻飞,如同大自然吟诵的一首抒情长诗,抒写着草木对大地的爱恋。生于斯,归于斯,岁岁轮回只为把深情一次次交付。
无边落木,萧萧而下。秋天深了,不只是季节底色的变化,也多了一些声响。风声越来越响,有时像叹息一样深沉,有时像哨音一样尖利。落叶簌簌而下,一阵风过,地上一层枯黄。秋风扫落叶的场面,颇有点震撼。深秋的风,仿佛一位武林高手,身怀绝技,杀伐决断,招招制敌。风只需扫上一圈,树上的枯叶就集体扑向大地,大地上的落叶也集体被裹挟在风中四处流浪,停到哪里算哪里。萧瑟秋风,把秋天推向了深处。
深秋的雨,一场寒似一场。风由凉到寒,这个过程看似自然而然,实则是一次质变。初秋时的雨,清爽舒适,尚有朗朗之气。而深秋的雨,摇身一变成了沧桑倦客,点点滴滴都是苍凉的味道,很容易让人想到蒋捷的词:“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我觉得深秋的雨就是那种“悲欢离合总无情”的感觉,让人无限唏嘘。
深秋的田野变得空旷起来,庄稼收完,草木枯萎,虫声隐匿,鸟影稀落。极目远眺,仿佛能望到天边。地平线清晰地把蓝天和厚土分割开来,有“天苍苍,野茫茫”的画面感。昔日热闹的土地上沉寂冷清,季节的繁华之门关闭了,我们只能在庄稼的余香里一遍遍地怀想。夕阳缓缓沉到西天,秋日深深深几许?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
秋深几许,苍凉满目。古人悲秋,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大自然在这时努力节制和收敛。一切都被删减,一切都被省略,为的是呈现一个简洁不芜杂的冬天。这样的转变,常常会让我们心理上产生落差,于是“悲秋”便成了人们情感表达的出口。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渴望温暖的慰藉,渴望简单的幸福。
待到冬天来临时,我们方才明白季节的良苦用心。深秋这段冷寂而萧瑟的时光,是为了提醒人们季节过渡,寒冷的冬季即将到来,提前做好准备。
秋深了,踏着季节的节拍,去留住秋天的最后一抹诗意吧……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930/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