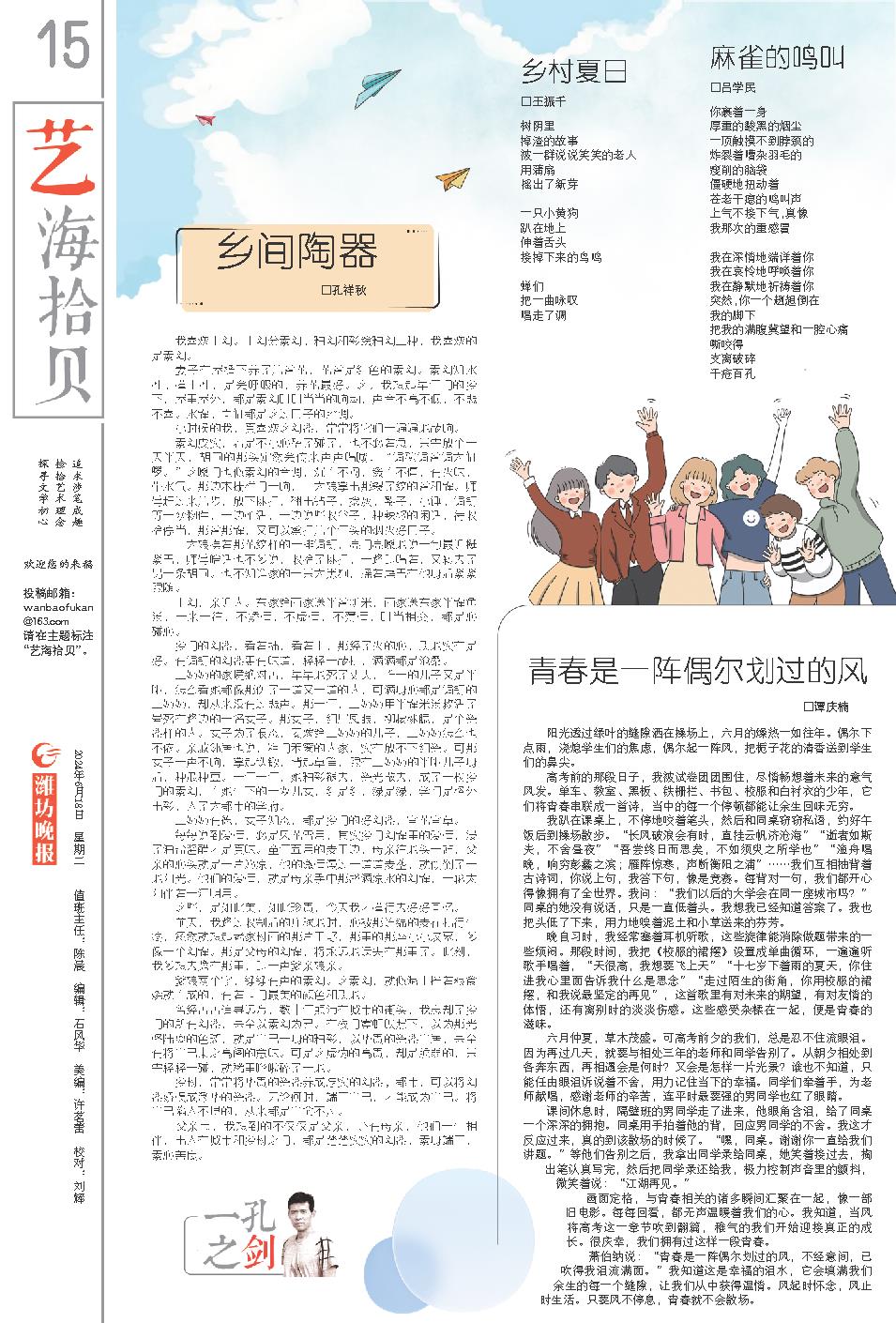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留住“绿色记忆”
 15版:艺海拾贝
15版:艺海拾贝
- * 乡间陶器
- * 乡村夏日
- * 麻雀的鸣叫
- * 青春是一阵偶尔划过的风
□孔祥秋
我喜欢土陶。土陶分素陶、釉陶和彩绘釉陶三种,我喜欢的是素陶。
妻子在屋檐下养了几盆花,花盆是红色的素陶。素陶知水性、懂土性,是会呼吸的,养花最好。这让我想起早年间的乡下,屋里屋外,都是素陶叮叮当当的响动,声音不高不低,不悲不喜。水罐、面缸都是这过日子的腔调。
小时候的我,真喜欢这陶器,常常将它们一遍遍地敲响。
素陶皮实,若是不小心磕了碰了,也不必着急,只需放个一天半天,胡同的那头定然会传来声声唱喊:“锔碗锔盆锔大缸啰。”这嗓门也似素陶的音调,沉而不闷,缓而不僵,有火味,带水气。那边木栅栏门一响,二大娘拿出那裂了纹的盆和罐。师傅赶过来几步,放下挑担,翻出钻子、捻灰、錾子、小锤、锔钉等一众物件,一边忙活,一边说些收谷子、种辣椒的闲话,待收拾停当,那盆那罐,又可以承担几个年头的烟火好日子。
二大娘摸着那花纹样的一排锔钉,亮门亮嗓地说一句最近挺紧巴,师傅啥话也不多说,收拾了挑担,一路叫唱着,又转去了另一条胡同。也不知谁家的一只大黑狗,摇着尾巴在他身后紧紧跟随。
土陶,亲近人。东家给西家送半盆新米,西家送东家半罐鱼汤,一来一往,不矫情,不虚情,不薄情,叮当相交,都是心碰心。
乡间的陶器,看着拙,看着土,那经了火的心,质地实在是好。有锔钉的陶器更有味道,轻轻一敲打,满满都是沧桑。
三奶奶的家境绝对苦,早早地死了丈夫,唯一的儿子又是半哑,怎么看她都像那伤了一道又一道的人,可满身心都是锔钉的三奶奶,却从来没有过悲声。那一年,三奶奶用半罐米汤救活了晕死在路边的一名女子。那女子,细眉凤眼,柳腰桃腮,是个瓷器样的人。女子为了报恩,要嫁给三奶奶的儿子,三奶奶怎么也不依。亲戚邻居也说,粗门笨窗的人家,实在放不下细瓷。可那女子一声不响,拿起铁锨,背起草筐,跟在三奶奶的半哑儿子身后,种瓜种豆。一年一年,她釉彩褪去,瓷光散去,成了一枚乡间的素陶,而她生下的一双儿女,红是红,绿是绿,学问是格外出彩,入了大都市的学府。
三奶奶有德,女子知恩,都是乡间的好陶器,宜花宜草。
每每说到爱情,必是风花雪月,其实乡间陶罐里的爱情,浸了油盐酱醋才是真味。童年五月的麦田边,母亲往地头一站,父亲的心头就是一片沁凉,他的激情漫过一道道麦垄,就倾倒了一地阳光。他们的爱情,就是母亲手中那盛满凉水的陶罐,一轮太阳伴着一汪明月。
这些,是如此美、如此珍贵,今天我才懂得去好好回忆。
前天,我路过收割后的庄稼地时,心被那连绵的麦茬扎得生疼,忽然就想起老家村西的那片田野,那里的那座小小坟墓,多像一个陶罐。那是父母的陶罐,将永远地遗失在那里了。此刻,我多想去跪在那里,叫一声爹亲娘亲。
爹娘两个字,铮铮有声的素陶。这素陶,就似泥土拌着粮食烧就而成的,有着世间最美的颜色和质地。
曾经苦苦追寻远方,数十年颠沛在城市的街头,我忘却了乡间的所有陶器,甚至以素陶为丑。在夜间霓虹映照下,以为那光怪陆离的色斑,就是自己一身的釉彩,以华贵的瓷器自居,甚至有将自己束之高阁的意味。可是这虚伪的高贵,却是脆弱的,只需轻轻一碰,就稀里哗啦碎了一地。
乡村,常常将华贵的瓷器养成厚实的陶器;都市,可以将陶器娇惯成浮华的瓷器。无论何时,端正自己,才能成为自己。将自己陷入不堪的,从来都是自命不凡。
父亲节,我想到的不仅仅是父亲,还有母亲,他们一生相伴,出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都是踏踏实实的陶器,素身端正,素心善良。
我喜欢土陶。土陶分素陶、釉陶和彩绘釉陶三种,我喜欢的是素陶。
妻子在屋檐下养了几盆花,花盆是红色的素陶。素陶知水性、懂土性,是会呼吸的,养花最好。这让我想起早年间的乡下,屋里屋外,都是素陶叮叮当当的响动,声音不高不低,不悲不喜。水罐、面缸都是这过日子的腔调。
小时候的我,真喜欢这陶器,常常将它们一遍遍地敲响。
素陶皮实,若是不小心磕了碰了,也不必着急,只需放个一天半天,胡同的那头定然会传来声声唱喊:“锔碗锔盆锔大缸啰。”这嗓门也似素陶的音调,沉而不闷,缓而不僵,有火味,带水气。那边木栅栏门一响,二大娘拿出那裂了纹的盆和罐。师傅赶过来几步,放下挑担,翻出钻子、捻灰、錾子、小锤、锔钉等一众物件,一边忙活,一边说些收谷子、种辣椒的闲话,待收拾停当,那盆那罐,又可以承担几个年头的烟火好日子。
二大娘摸着那花纹样的一排锔钉,亮门亮嗓地说一句最近挺紧巴,师傅啥话也不多说,收拾了挑担,一路叫唱着,又转去了另一条胡同。也不知谁家的一只大黑狗,摇着尾巴在他身后紧紧跟随。
土陶,亲近人。东家给西家送半盆新米,西家送东家半罐鱼汤,一来一往,不矫情,不虚情,不薄情,叮当相交,都是心碰心。
乡间的陶器,看着拙,看着土,那经了火的心,质地实在是好。有锔钉的陶器更有味道,轻轻一敲打,满满都是沧桑。
三奶奶的家境绝对苦,早早地死了丈夫,唯一的儿子又是半哑,怎么看她都像那伤了一道又一道的人,可满身心都是锔钉的三奶奶,却从来没有过悲声。那一年,三奶奶用半罐米汤救活了晕死在路边的一名女子。那女子,细眉凤眼,柳腰桃腮,是个瓷器样的人。女子为了报恩,要嫁给三奶奶的儿子,三奶奶怎么也不依。亲戚邻居也说,粗门笨窗的人家,实在放不下细瓷。可那女子一声不响,拿起铁锨,背起草筐,跟在三奶奶的半哑儿子身后,种瓜种豆。一年一年,她釉彩褪去,瓷光散去,成了一枚乡间的素陶,而她生下的一双儿女,红是红,绿是绿,学问是格外出彩,入了大都市的学府。
三奶奶有德,女子知恩,都是乡间的好陶器,宜花宜草。
每每说到爱情,必是风花雪月,其实乡间陶罐里的爱情,浸了油盐酱醋才是真味。童年五月的麦田边,母亲往地头一站,父亲的心头就是一片沁凉,他的激情漫过一道道麦垄,就倾倒了一地阳光。他们的爱情,就是母亲手中那盛满凉水的陶罐,一轮太阳伴着一汪明月。
这些,是如此美、如此珍贵,今天我才懂得去好好回忆。
前天,我路过收割后的庄稼地时,心被那连绵的麦茬扎得生疼,忽然就想起老家村西的那片田野,那里的那座小小坟墓,多像一个陶罐。那是父母的陶罐,将永远地遗失在那里了。此刻,我多想去跪在那里,叫一声爹亲娘亲。
爹娘两个字,铮铮有声的素陶。这素陶,就似泥土拌着粮食烧就而成的,有着世间最美的颜色和质地。
曾经苦苦追寻远方,数十年颠沛在城市的街头,我忘却了乡间的所有陶器,甚至以素陶为丑。在夜间霓虹映照下,以为那光怪陆离的色斑,就是自己一身的釉彩,以华贵的瓷器自居,甚至有将自己束之高阁的意味。可是这虚伪的高贵,却是脆弱的,只需轻轻一碰,就稀里哗啦碎了一地。
乡村,常常将华贵的瓷器养成厚实的陶器;都市,可以将陶器娇惯成浮华的瓷器。无论何时,端正自己,才能成为自己。将自己陷入不堪的,从来都是自命不凡。
父亲节,我想到的不仅仅是父亲,还有母亲,他们一生相伴,出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都是踏踏实实的陶器,素身端正,素心善良。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18/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