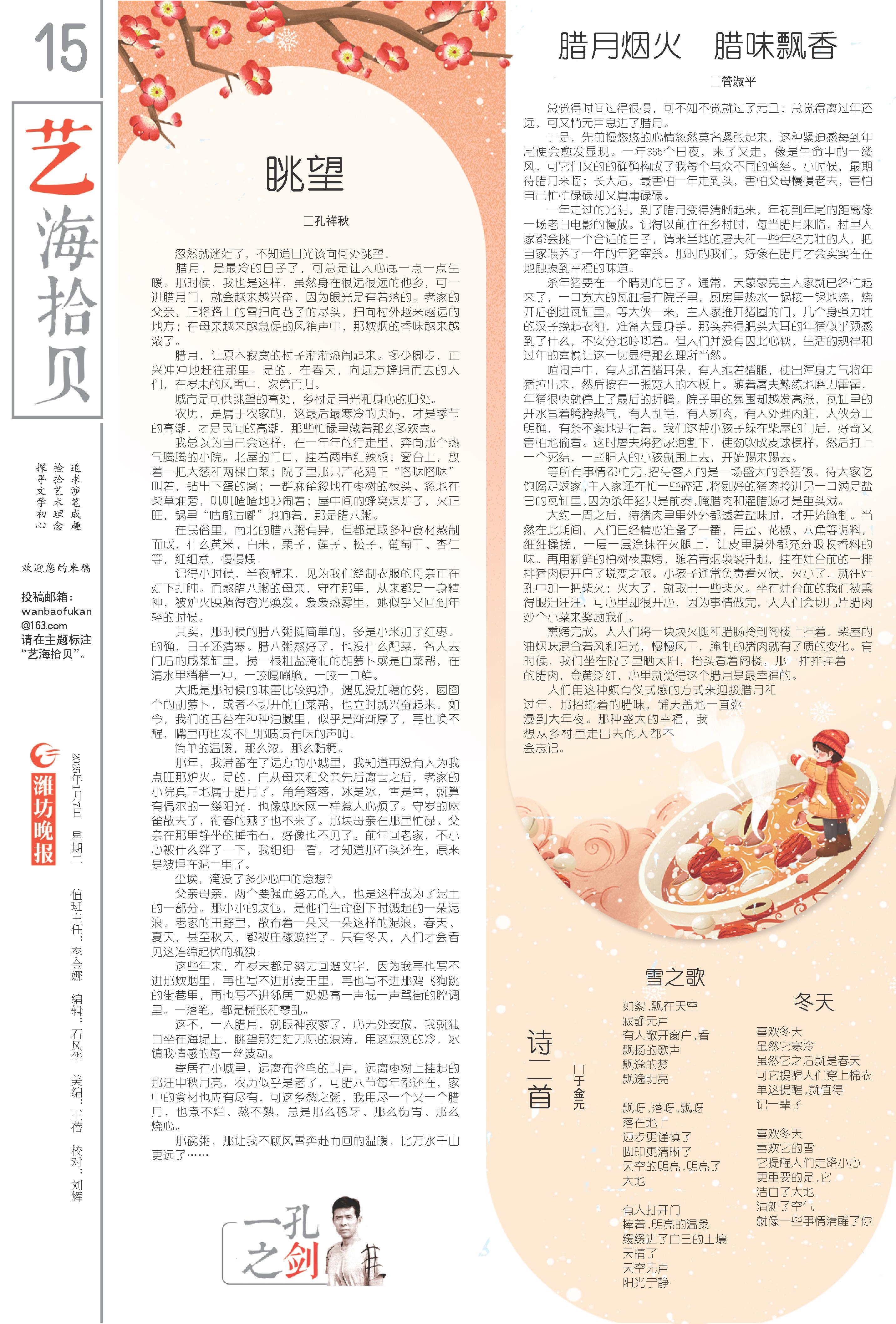11版:康养周刊
11版:康养周刊
- * 迟发性运动障碍 您了解吗
- * 如何“呵护”前列腺
- *
查出肺结节
不必太纠结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眺望远方
□孔祥秋
忽然就迷茫了,不知道目光该向何处眺望。
腊月,是最冷的日子了,可总是让人心底一点一点生暖。那时候,我也是这样,虽然身在很远很远的他乡,可一进腊月门,就会越来越兴奋,因为眼光是有着落的。老家的父亲,正将路上的雪扫向巷子的尽头,扫向村外越来越远的地方;在母亲越来越急促的风箱声中,那炊烟的香味越来越浓了。
腊月,让原本寂寞的村子渐渐热闹起来。多少脚步,正兴冲冲地赶往那里。是的,在春天,向远方蜂拥而去的人们,在岁末的风雪中,次第而归。
城市是可供眺望的高处,乡村是目光和身心的归处。
农历,是属于农家的,这最后最寒冷的页码,才是季节的高潮,才是民间的高潮,那些忙碌里藏着那么多欢喜。
我总以为自己会这样,在一年年的行走里,奔向那个热气腾腾的小院。北屋的门口,挂着两串红辣椒;窗台上,放着一把大葱和两棵白菜;院子里那只芦花鸡正“咯哒咯哒”叫着,钻出下蛋的窝;一群麻雀忽地在枣树的枝头、忽地在柴草堆旁,叽叽喳喳地吵闹着;屋中间的蜂窝煤炉子,火正旺,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着,那是腊八粥。
在民俗里,南北的腊八粥有异,但都是取多种食材熬制而成,什么黄米、白米、栗子、莲子、松子、葡萄干、杏仁等,细细煮,慢慢煨。
记得小时候,半夜醒来,见为我们缝制衣服的母亲正在灯下打盹。而熬腊八粥的母亲,守在那里,从来都是一身精神,被炉火映照得容光焕发。袅袅热雾里,她似乎又回到年轻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的腊八粥挺简单的,多是小米加了红枣。的确,日子还清寒。腊八粥熬好了,也没什么配菜,各人去门后的咸菜缸里,捞一根粗盐腌制的胡萝卜或是白菜帮,在清水里稍稍一冲,一咬嘎嘣脆,一咬一口鲜。
大抵是那时候的味蕾比较纯净,遇见没加糖的粥,囫囵个的胡萝卜,或者不切开的白菜帮,也立时就兴奋起来。如今,我们的舌苔在种种油腻里,似乎是渐渐厚了,再也唤不醒,嘴里再也发不出那啧啧有味的声响。
简单的温暖,那么浓,那么黏稠。
那年,我滞留在了远方的小城里,我知道再没有人为我点旺那炉火。是的,自从母亲和父亲先后离世之后,老家的小院真正地属于腊月了,角角落落,冰是冰,雪是雪,就算有偶尔的一缕阳光,也像蜘蛛网一样惹人心烦了。守岁的麻雀散去了,衔春的燕子也不来了。那块母亲在那里忙碌、父亲在那里静坐的捶布石,好像也不见了。前年回老家,不小心被什么绊了一下,我细细一看,才知道那石头还在,原来是被埋在泥土里了。
尘埃,淹没了多少心中的念想?
父亲母亲,两个要强而努力的人,也是这样成为了泥土的一部分。那小小的坟包,是他们生命倒下时溅起的一朵泥浪。老家的田野里,散布着一朵又一朵这样的泥浪,春天、夏天,甚至秋天,都被庄稼遮挡了。只有冬天,人们才会看见这连绵起伏的孤独。
这些年来,在岁末都是努力回避文字,因为我再也写不进那炊烟里,再也写不进那麦田里,再也写不进那鸡飞狗跳的街巷里,再也写不进邻居二奶奶高一声低一声骂街的腔调里。一落笔,都是慌张和零乱。
这不,一入腊月,就眼神寂寥了,心无处安放,我就独自坐在海堤上,眺望那茫茫无际的浪涛,用这凛冽的冷,冰镇我情感的每一丝波动。
寄居在小城里,远离布谷鸟的叫声,远离枣树上挂起的那汪中秋月亮,农历似乎是老了,可腊八节每年都还在,家中的食材也应有尽有,可这乡愁之粥,我用尽一个又一个腊月,也煮不烂、熬不熟,总是那么硌牙、那么伤胃、那么烧心。
那碗粥,那让我不顾风雪奔赴而回的温暖,比万水千山更远了……
忽然就迷茫了,不知道目光该向何处眺望。
腊月,是最冷的日子了,可总是让人心底一点一点生暖。那时候,我也是这样,虽然身在很远很远的他乡,可一进腊月门,就会越来越兴奋,因为眼光是有着落的。老家的父亲,正将路上的雪扫向巷子的尽头,扫向村外越来越远的地方;在母亲越来越急促的风箱声中,那炊烟的香味越来越浓了。
腊月,让原本寂寞的村子渐渐热闹起来。多少脚步,正兴冲冲地赶往那里。是的,在春天,向远方蜂拥而去的人们,在岁末的风雪中,次第而归。
城市是可供眺望的高处,乡村是目光和身心的归处。
农历,是属于农家的,这最后最寒冷的页码,才是季节的高潮,才是民间的高潮,那些忙碌里藏着那么多欢喜。
我总以为自己会这样,在一年年的行走里,奔向那个热气腾腾的小院。北屋的门口,挂着两串红辣椒;窗台上,放着一把大葱和两棵白菜;院子里那只芦花鸡正“咯哒咯哒”叫着,钻出下蛋的窝;一群麻雀忽地在枣树的枝头、忽地在柴草堆旁,叽叽喳喳地吵闹着;屋中间的蜂窝煤炉子,火正旺,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着,那是腊八粥。
在民俗里,南北的腊八粥有异,但都是取多种食材熬制而成,什么黄米、白米、栗子、莲子、松子、葡萄干、杏仁等,细细煮,慢慢煨。
记得小时候,半夜醒来,见为我们缝制衣服的母亲正在灯下打盹。而熬腊八粥的母亲,守在那里,从来都是一身精神,被炉火映照得容光焕发。袅袅热雾里,她似乎又回到年轻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的腊八粥挺简单的,多是小米加了红枣。的确,日子还清寒。腊八粥熬好了,也没什么配菜,各人去门后的咸菜缸里,捞一根粗盐腌制的胡萝卜或是白菜帮,在清水里稍稍一冲,一咬嘎嘣脆,一咬一口鲜。
大抵是那时候的味蕾比较纯净,遇见没加糖的粥,囫囵个的胡萝卜,或者不切开的白菜帮,也立时就兴奋起来。如今,我们的舌苔在种种油腻里,似乎是渐渐厚了,再也唤不醒,嘴里再也发不出那啧啧有味的声响。
简单的温暖,那么浓,那么黏稠。
那年,我滞留在了远方的小城里,我知道再没有人为我点旺那炉火。是的,自从母亲和父亲先后离世之后,老家的小院真正地属于腊月了,角角落落,冰是冰,雪是雪,就算有偶尔的一缕阳光,也像蜘蛛网一样惹人心烦了。守岁的麻雀散去了,衔春的燕子也不来了。那块母亲在那里忙碌、父亲在那里静坐的捶布石,好像也不见了。前年回老家,不小心被什么绊了一下,我细细一看,才知道那石头还在,原来是被埋在泥土里了。
尘埃,淹没了多少心中的念想?
父亲母亲,两个要强而努力的人,也是这样成为了泥土的一部分。那小小的坟包,是他们生命倒下时溅起的一朵泥浪。老家的田野里,散布着一朵又一朵这样的泥浪,春天、夏天,甚至秋天,都被庄稼遮挡了。只有冬天,人们才会看见这连绵起伏的孤独。
这些年来,在岁末都是努力回避文字,因为我再也写不进那炊烟里,再也写不进那麦田里,再也写不进那鸡飞狗跳的街巷里,再也写不进邻居二奶奶高一声低一声骂街的腔调里。一落笔,都是慌张和零乱。
这不,一入腊月,就眼神寂寥了,心无处安放,我就独自坐在海堤上,眺望那茫茫无际的浪涛,用这凛冽的冷,冰镇我情感的每一丝波动。
寄居在小城里,远离布谷鸟的叫声,远离枣树上挂起的那汪中秋月亮,农历似乎是老了,可腊八节每年都还在,家中的食材也应有尽有,可这乡愁之粥,我用尽一个又一个腊月,也煮不烂、熬不熟,总是那么硌牙、那么伤胃、那么烧心。
那碗粥,那让我不顾风雪奔赴而回的温暖,比万水千山更远了……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07/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