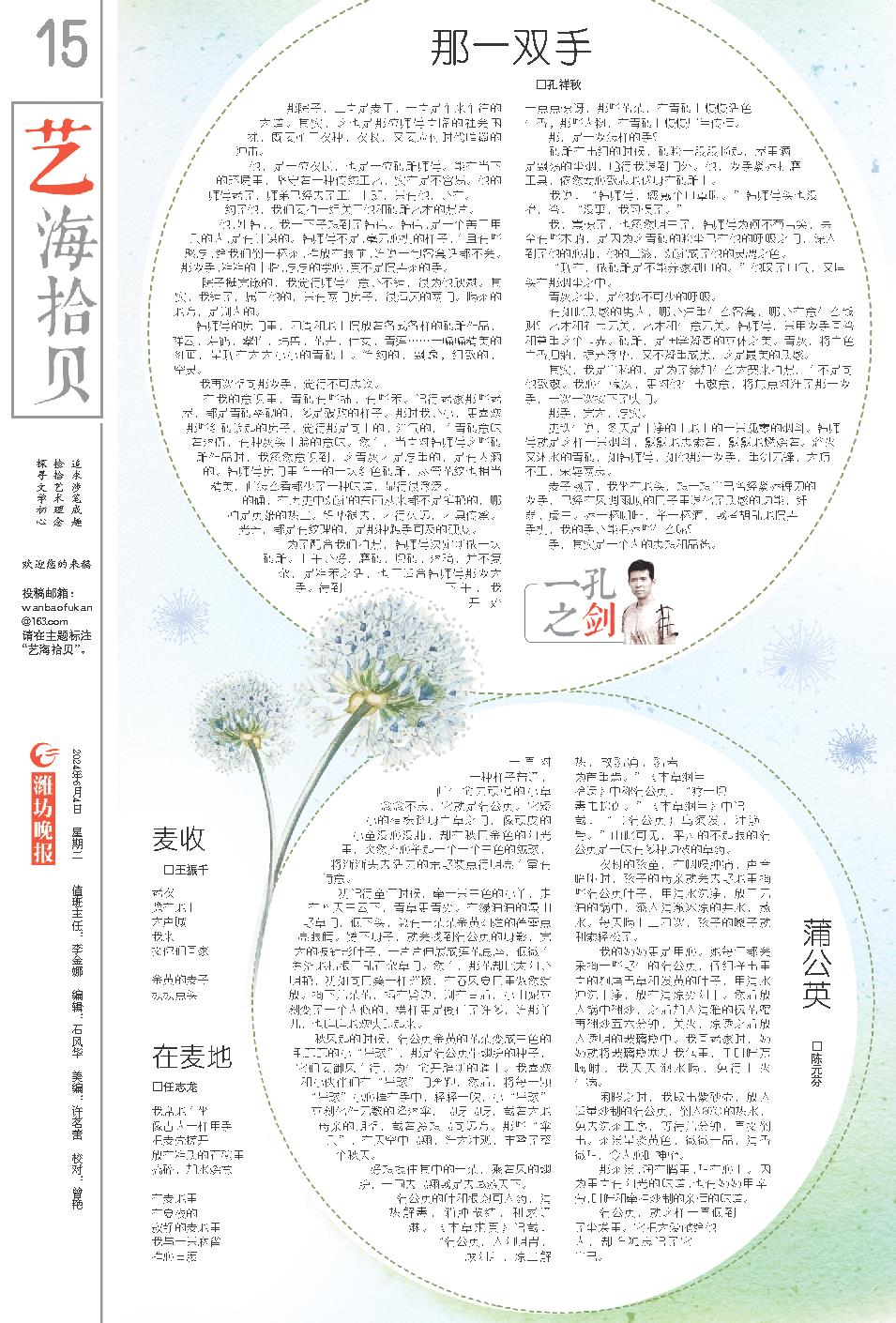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武动乾坤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船在画中游
□孔祥秋
那院子,三面是麦田,一面是车来车往的大道。其实,这也是那位师傅面临的社会困扰,既要忙于农种、农收,又要应付时代喧嚣的冲击。
他,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位砖雕师傅。能在当下的环境里,坚守着一种传统工艺,实在是不容易。他的师傅老了,师弟已经去了工厂上班,只有他,还在。
约了他,我们要拍一组关于他和砖雕艺术的照片。
他,姓韩,让我一下子想到了韩信。韩信,是一个善于用兵的人,是有计谋的。韩师傅不是,毫无心机的样子,而且有些憨厚,给我们倒一杯茶,推放在眼前,连说一句客套话都不会。那双手,粗粗的十指,厚厚的掌心,真不是摆弄茶的手。
院子挺宽敞的,我觉得师傅生意还不错,很为他欣慰。其实,我错了,属于他的,只有两间房子,很逼仄的两间。喝茶的地方,是别人的。
韩师傅的房间里,四周和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砖雕作品,祥云、寿鹤、翠竹、瑞兽、花卉、仕女、青莲……一幅幅精美的图画,呈现在大大小小的青砖上。简约的,飘逸;细致的,空灵。
我再次望向那双手,觉得不可思议。
在我的意识里,青砖有些拙、有些笨。记得老家那些老屋,都是青砖垒砌的,多是破败的样子。那时我还小,更喜欢那些红砖筑起的房子,觉得那是向上的、洋气的,而青砖意味着落伍,有种灰头土脸的意味。然而,当面对韩师傅这些砖雕作品时,我忽然意识到,这青灰才是厚重的,是有内涵的。韩师傅房间里唯一的一块红色砖雕,尽管花纹也相当精美,但怎么看都少了一种味道,显得很浮泛。
的确,在历史中沉淀的东西从来都不是鲜艳的,哪怕是英雄的热血。铅华褪去,才得久远,才具传承。光芒,都是有纹理的,是那种触手可及的硬度。
为了配合我们拍照,韩师傅决定新做一块砖雕。上午还好,磨砖、切砖、落稿,并不复杂,是粗笨之活,也正适合韩师傅那双大手。待到下午,我开始一点点惊讶,那些花朵,在青砖上慢慢活色生香;那些人物,在青砖上慢慢眉目传情。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
砖雕在出细的时候,砖粉一股股扬起,屋里满是飘荡的尘烟,呛得我退到门外。他,双手紧握打磨工具,依然专心致志地伏身在砖雕上。
我说:“韩师傅,您戴个口罩啊。”韩师傅头也没抬,答:“没事,我习惯了。”
我,震惊了,也忽然明白了,韩师傅为何不苟言笑,甚至有些木讷,是因为这青砖的粉尘已在他的呼吸之间,深入到了他的心肺、他的血液,沉淀成了他的灵魂之色。
“现在,做砖雕是不能养家糊口的。”他叹了口气,又埋头在那烟尘之中。
青灰之尘,是他必不可少的呼吸。
有如此质感的男人,哪还注重什么客套,哪还在意什么钱财?艺术和礼节无关,艺术和生意无关。韩师傅,只用双手回答和尊重这个世界。砖雕,是国学凝固的立体之美。青灰,将百色百香归纳,摒弃浮华,又不凝重成黑,这是最美的质感。
其实,我是自私的,是为了参加什么大赛来拍照,而不是向他致敬。我心生愧疚,更对他生出敬意,将焦点对准了那一双手,一次一次按下了快门。
那手,宽大,厚实。
史铁生说,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韩师傅就是这样一只烟斗,默默地思索着,默默地燃烧着。浴火又沐水的青砖,如韩师傅,如他那一双手,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荣辱两忘。
麦子熟了,我坐在地头,想一想自己曾经紧握镰刀的双手,已经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退化了质感的功能,纤弱、虚白。握一杯咖啡,举一杯酒,或者胡乱地摆弄手机,我的手还能把握些什么呢?
手,其实是一个人的思想和品德。
那院子,三面是麦田,一面是车来车往的大道。其实,这也是那位师傅面临的社会困扰,既要忙于农种、农收,又要应付时代喧嚣的冲击。
他,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位砖雕师傅。能在当下的环境里,坚守着一种传统工艺,实在是不容易。他的师傅老了,师弟已经去了工厂上班,只有他,还在。
约了他,我们要拍一组关于他和砖雕艺术的照片。
他,姓韩,让我一下子想到了韩信。韩信,是一个善于用兵的人,是有计谋的。韩师傅不是,毫无心机的样子,而且有些憨厚,给我们倒一杯茶,推放在眼前,连说一句客套话都不会。那双手,粗粗的十指,厚厚的掌心,真不是摆弄茶的手。
院子挺宽敞的,我觉得师傅生意还不错,很为他欣慰。其实,我错了,属于他的,只有两间房子,很逼仄的两间。喝茶的地方,是别人的。
韩师傅的房间里,四周和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砖雕作品,祥云、寿鹤、翠竹、瑞兽、花卉、仕女、青莲……一幅幅精美的图画,呈现在大大小小的青砖上。简约的,飘逸;细致的,空灵。
我再次望向那双手,觉得不可思议。
在我的意识里,青砖有些拙、有些笨。记得老家那些老屋,都是青砖垒砌的,多是破败的样子。那时我还小,更喜欢那些红砖筑起的房子,觉得那是向上的、洋气的,而青砖意味着落伍,有种灰头土脸的意味。然而,当面对韩师傅这些砖雕作品时,我忽然意识到,这青灰才是厚重的,是有内涵的。韩师傅房间里唯一的一块红色砖雕,尽管花纹也相当精美,但怎么看都少了一种味道,显得很浮泛。
的确,在历史中沉淀的东西从来都不是鲜艳的,哪怕是英雄的热血。铅华褪去,才得久远,才具传承。光芒,都是有纹理的,是那种触手可及的硬度。
为了配合我们拍照,韩师傅决定新做一块砖雕。上午还好,磨砖、切砖、落稿,并不复杂,是粗笨之活,也正适合韩师傅那双大手。待到下午,我开始一点点惊讶,那些花朵,在青砖上慢慢活色生香;那些人物,在青砖上慢慢眉目传情。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
砖雕在出细的时候,砖粉一股股扬起,屋里满是飘荡的尘烟,呛得我退到门外。他,双手紧握打磨工具,依然专心致志地伏身在砖雕上。
我说:“韩师傅,您戴个口罩啊。”韩师傅头也没抬,答:“没事,我习惯了。”
我,震惊了,也忽然明白了,韩师傅为何不苟言笑,甚至有些木讷,是因为这青砖的粉尘已在他的呼吸之间,深入到了他的心肺、他的血液,沉淀成了他的灵魂之色。
“现在,做砖雕是不能养家糊口的。”他叹了口气,又埋头在那烟尘之中。
青灰之尘,是他必不可少的呼吸。
有如此质感的男人,哪还注重什么客套,哪还在意什么钱财?艺术和礼节无关,艺术和生意无关。韩师傅,只用双手回答和尊重这个世界。砖雕,是国学凝固的立体之美。青灰,将百色百香归纳,摒弃浮华,又不凝重成黑,这是最美的质感。
其实,我是自私的,是为了参加什么大赛来拍照,而不是向他致敬。我心生愧疚,更对他生出敬意,将焦点对准了那一双手,一次一次按下了快门。
那手,宽大,厚实。
史铁生说,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韩师傅就是这样一只烟斗,默默地思索着,默默地燃烧着。浴火又沐水的青砖,如韩师傅,如他那一双手,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荣辱两忘。
麦子熟了,我坐在地头,想一想自己曾经紧握镰刀的双手,已经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退化了质感的功能,纤弱、虚白。握一杯咖啡,举一杯酒,或者胡乱地摆弄手机,我的手还能把握些什么呢?
手,其实是一个人的思想和品德。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604/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