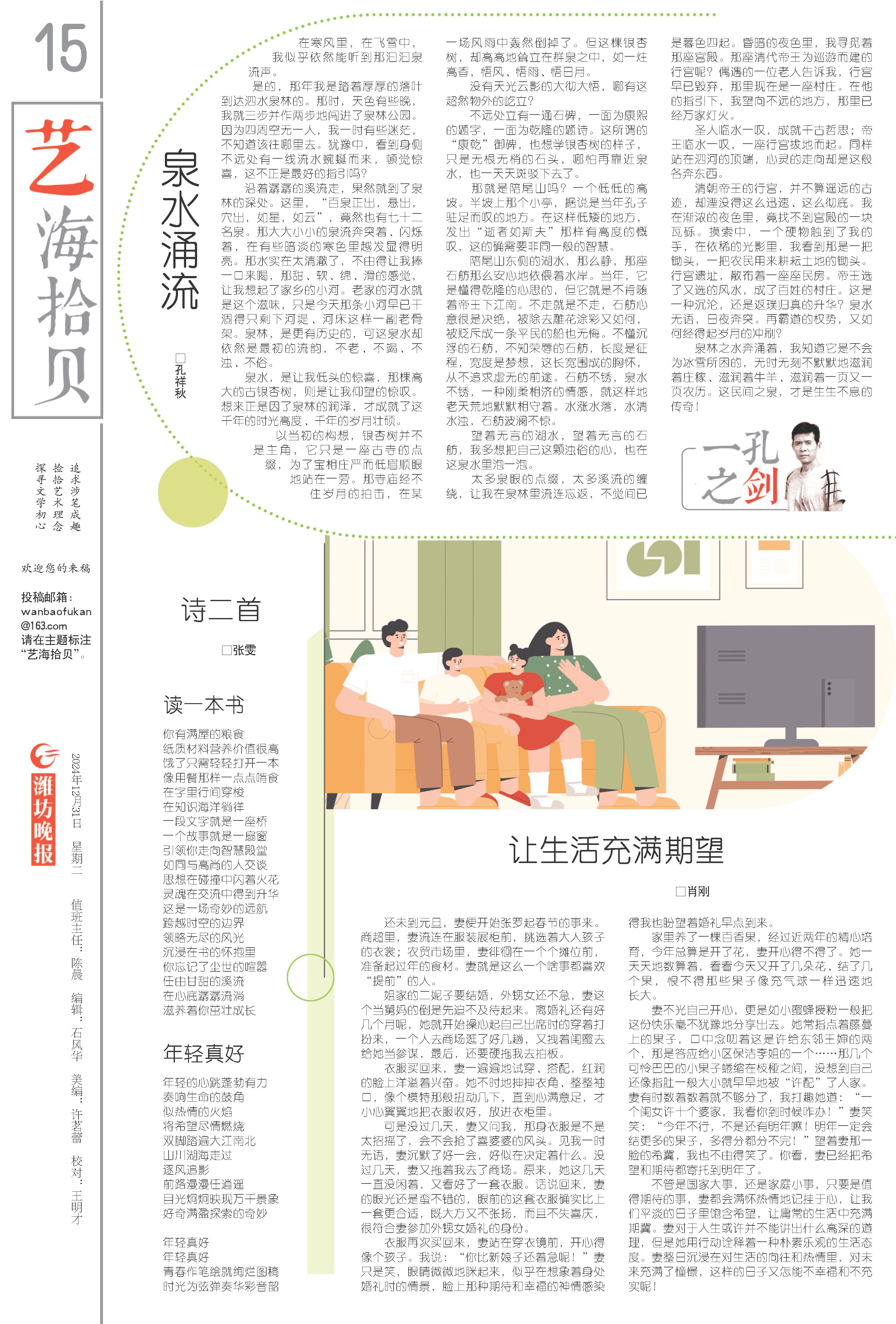07版:风筝之爱
07版:风筝之爱
- *
暖冬行动
送去关爱 - *
老人丢户口簿
志愿者伸援手 - *
爱心图书
发往西藏 - *
点亮微心愿
共筑童心梦 - *
便民利民
服务上门 - * 致全市医保参保人的一封信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期待明天
□孔祥秋
在寒风里,在飞雪中,我似乎依然能听到那汩汩泉流声。
是的,那年我是踏着厚厚的落叶到达泗水泉林的。那时,天色有些晚,我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闯进了泉林公园。因为四周空无一人,我一时有些迷茫,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犹豫中,看到身侧不远处有一线流水蜿蜒而来,顿觉惊喜,这不正是最好的指引吗?
沿着潺潺的溪流走,果然就到了泉林的深处。这里,“百泉正出,悬出,穴出,如星,如云”,竟然也有七十二名泉。那大大小小的泉流奔突着、闪烁着,在有些暗淡的寒色里越发显得明亮。那水实在太清澈了,不由得让我捧一口来喝,那甜、软、绵、滑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小河。老家的河水就是这个滋味,只是今天那条小河早已干涸得只剩下河堤、河床这样一副老骨架。泉林,是更有历史的,可这泉水却依然是最初的流韵,不老、不竭、不浊、不俗。
泉水,是让我低头的惊喜,那棵高大的古银杏树,则是让我仰望的惊叹。想来正是因了泉林的润泽,才成就了这千年的时光高度、千年的岁月壮硕。
以当初的构想,银杏树并不是主角,它只是一座古寺的点缀,为了宝相庄严而低眉顺眼地站在一旁。那寺庙经不住岁月的拍击,在某一场风雨中轰然倒掉了。但这棵银杏树,却高高地耸立在群泉之中,如一炷高香,悟风、悟雨、悟日月。
没有天光云影的大彻大悟,哪有这超然物外的屹立?
不远处立有一通石碑,一面为康熙的题字,一面为乾隆的题诗。这所谓的“康乾”御碑,也想学银杏树的样子,只是无根无梢的石头,哪怕再靠近泉水,也一天天斑驳下去了。
那就是陪尾山吗?一个低低的高坡。半坡上那个小亭,据说是当年孔子驻足而叹的地方。在这样低矮的地方,发出“逝者如斯夫”那样有高度的慨叹,这的确需要非同一般的智慧。
陪尾山东侧的湖水,那么静,那座石舫那么安心地依偎着水岸。当年,它是懂得乾隆的心思的,但它就是不肯随着帝王下江南。不走就是不走,石舫心意很是决绝,被除去雕花涂彩又如何,被贬斥成一条平民的船也无悔。不懂沉浮的石舫,不知荣辱的石舫,长度是征程,宽度是梦想,这长宽围成的胸怀,从不追求虚无的前途。石舫不锈,泉水不锈,一种刚柔相济的情感,就这样地老天荒地默默相守着。水涨水落,水清水浊,石舫波澜不惊。
望着无言的湖水,望着无言的石舫,我多想把自己这颗浊俗的心,也在这泉水里泡一泡。
太多泉眼的点缀,太多溪流的缠绕,让我在泉林里流连忘返,不觉间已是暮色四起。昏暗的夜色里,我寻觅着那座宫殿。那座清代帝王为巡游而建的行宫呢?偶遇的一位老人告诉我,行宫早已毁弃,那里现在是一座村庄。在他的指引下,我望向不远的地方,那里已经万家灯火。
圣人临水一叹,成就千古哲思;帝王临水一叹,一座行宫拔地而起。同样站在泗河的顶端,心灵的走向却是这般各奔东西。
清朝帝王的行宫,并不算遥远的古迹,却湮没得这么迅速、这么彻底。我在渐浓的夜色里,竟找不到宫殿的一块瓦砾。摸索中,一个硬物触到了我的手,在依稀的光影里,我看到那是一把锄头,一把农民用来耕耘土地的锄头。行宫遗址,散布着一座座民房。帝王选了又选的风水,成了百姓的村庄。这是一种沉沦,还是返璞归真的升华?泉水无语,日夜奔突。再霸道的权势,又如何经得起岁月的冲刷?
泉林之水奔涌着,我知道它是不会为冰雪所困的,无时无刻不默默地滋润着庄稼、滋润着牛羊、滋润着一页又一页农历。这民间之泉,才是生生不息的传奇!
在寒风里,在飞雪中,我似乎依然能听到那汩汩泉流声。
是的,那年我是踏着厚厚的落叶到达泗水泉林的。那时,天色有些晚,我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闯进了泉林公园。因为四周空无一人,我一时有些迷茫,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犹豫中,看到身侧不远处有一线流水蜿蜒而来,顿觉惊喜,这不正是最好的指引吗?
沿着潺潺的溪流走,果然就到了泉林的深处。这里,“百泉正出,悬出,穴出,如星,如云”,竟然也有七十二名泉。那大大小小的泉流奔突着、闪烁着,在有些暗淡的寒色里越发显得明亮。那水实在太清澈了,不由得让我捧一口来喝,那甜、软、绵、滑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小河。老家的河水就是这个滋味,只是今天那条小河早已干涸得只剩下河堤、河床这样一副老骨架。泉林,是更有历史的,可这泉水却依然是最初的流韵,不老、不竭、不浊、不俗。
泉水,是让我低头的惊喜,那棵高大的古银杏树,则是让我仰望的惊叹。想来正是因了泉林的润泽,才成就了这千年的时光高度、千年的岁月壮硕。
以当初的构想,银杏树并不是主角,它只是一座古寺的点缀,为了宝相庄严而低眉顺眼地站在一旁。那寺庙经不住岁月的拍击,在某一场风雨中轰然倒掉了。但这棵银杏树,却高高地耸立在群泉之中,如一炷高香,悟风、悟雨、悟日月。
没有天光云影的大彻大悟,哪有这超然物外的屹立?
不远处立有一通石碑,一面为康熙的题字,一面为乾隆的题诗。这所谓的“康乾”御碑,也想学银杏树的样子,只是无根无梢的石头,哪怕再靠近泉水,也一天天斑驳下去了。
那就是陪尾山吗?一个低低的高坡。半坡上那个小亭,据说是当年孔子驻足而叹的地方。在这样低矮的地方,发出“逝者如斯夫”那样有高度的慨叹,这的确需要非同一般的智慧。
陪尾山东侧的湖水,那么静,那座石舫那么安心地依偎着水岸。当年,它是懂得乾隆的心思的,但它就是不肯随着帝王下江南。不走就是不走,石舫心意很是决绝,被除去雕花涂彩又如何,被贬斥成一条平民的船也无悔。不懂沉浮的石舫,不知荣辱的石舫,长度是征程,宽度是梦想,这长宽围成的胸怀,从不追求虚无的前途。石舫不锈,泉水不锈,一种刚柔相济的情感,就这样地老天荒地默默相守着。水涨水落,水清水浊,石舫波澜不惊。
望着无言的湖水,望着无言的石舫,我多想把自己这颗浊俗的心,也在这泉水里泡一泡。
太多泉眼的点缀,太多溪流的缠绕,让我在泉林里流连忘返,不觉间已是暮色四起。昏暗的夜色里,我寻觅着那座宫殿。那座清代帝王为巡游而建的行宫呢?偶遇的一位老人告诉我,行宫早已毁弃,那里现在是一座村庄。在他的指引下,我望向不远的地方,那里已经万家灯火。
圣人临水一叹,成就千古哲思;帝王临水一叹,一座行宫拔地而起。同样站在泗河的顶端,心灵的走向却是这般各奔东西。
清朝帝王的行宫,并不算遥远的古迹,却湮没得这么迅速、这么彻底。我在渐浓的夜色里,竟找不到宫殿的一块瓦砾。摸索中,一个硬物触到了我的手,在依稀的光影里,我看到那是一把锄头,一把农民用来耕耘土地的锄头。行宫遗址,散布着一座座民房。帝王选了又选的风水,成了百姓的村庄。这是一种沉沦,还是返璞归真的升华?泉水无语,日夜奔突。再霸道的权势,又如何经得起岁月的冲刷?
泉林之水奔涌着,我知道它是不会为冰雪所困的,无时无刻不默默地滋润着庄稼、滋润着牛羊、滋润着一页又一页农历。这民间之泉,才是生生不息的传奇!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31/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