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硬核”暑假
 05版:社会新闻
05版:社会新闻
- * 野生蘑菇不要采更不要吃
- * 小小消防员
- *
接到民警电话
粗心爸爸方知丢了娃 - *
寻回4.3万元救命钱
民警给老人送上门 - * 公益广告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八月 驰骋在草原
□孔祥秋
故乡有荷也有柳。荷在水,柳在岸,荷凭水而美,柳舞风而媚。
夏日的校园,荷香悠悠,杨柳依依。在这里,少年的我,读到了那首《如梦令》。读了,就心生喜欢。想这写词的女子,笔下有荷,她那里,也必定有柳。那绿荫掩映的门楣,就是她的家。不远处,是让她醉而忘归的荷塘,那里鸥鸟翔集。
在我的意念里,李清照身似翠柳,心有荷香,梦如轻舟。后来,知晓她的老家就在济南的泉水边,也就更坚定了这种想法。甚至一度无来由地认为,柳泉居士的别号应属于李清照,而不是蒲松龄。想那说狐论妖的蒲老爷子,穷困潦倒,年高体衰,怎么能有这样柳新泉明的别号呢?太不相宜,太不相宜了。终究是,李清照的家,有柳亦有泉。柳色泉影,柳泉居士这别号,更适合这个宋朝的女子。清澈、飘逸、自在,多好!
为此,我臆想着如果有机会去往淄川,真希望能遇到那个在街头煮茶待客索故事的蒲老先生,和他说说这别号的事。我想,他一定会捋着胡子、笑着朝我点点头。当然,他也会舍我一杯茶,尽管我不会说鬼故事给他。那茶,可是柳叶茶么?反正他笔下的故事,大都似柳叶茶,苦而败火。
那时候,对于鬼妖我还是有所畏怕的,从同学家借来《聊斋志异》,也没怎么敢看。那书是竖排的繁体字,对我来说也的确读不扎实,再加上那泛黄的纸页,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所以很快就还了回去。即便如此,对于说鬼说妖的蒲松龄先生,却没有丝毫惧意,想来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毕竟我们村东头那个独居的本家爷爷,就常常用鬼怪的说词来逗弄我们,可他更愿意用他家树上结的各种果子来哄我们开心。
蒲松龄应该也是这样一个老头,惹人惊心,又让人欢喜。
明水,一听这名字,波光粼粼的,就感觉满是灵气,轻轻一念读,舌尖上就滑过丝绸般的柔爽。这个济南章丘的小镇,和诸多的小镇一样,既有城的富足和喧闹,也有村的朴实和忙碌,镶嵌在大片大片的田野中,像一块雕花的玉。相传,在明水有三处水量丰沛的泉眼,因为各在三户殷实人家,不为常人所见,所以被称“三不露”。其中一户就是李家,这李家,就是李清照的家。据说,她的名字就取自这泉水的波光闪烁。
上天的灵感,自是不同凡响。如此,这个出生于小镇的女孩,从小沐浴着清泉水般的宠爱,俨然就有了泉水一样活泼的灵魂,不拘教条;也就有了泉水一样清澈的才情,艳冠群芳。她的性格就像这小镇,亦城亦乡,既华贵,又泼辣。静,就守着泉眼出神,入痴入禅,像一朵荷;动,就追着泉水奔跑,翻沟越坎,像一缕风。
从青砖灰瓦的巷子里走出来,她一路成长。不远的田野里是大片的麦子,也有一丛丛杨柳、桃李或是桑林。那是一片悠游自在的天地。应当是就此成就了李清照的婉约与豪放。
当小小的她随着父亲来到东京汴梁,面对这个堆金叠玉的城,面对这个群英荟萃的城,没有丝毫胆怯。更是在名流云集的诗词场合,抑扬顿挫地张扬着自己,以称赞“梅定妒,菊应羞”的桂花为由头,暗喻自己“自是花中第一流”。可她遇了那个男子,又有了“和羞走”的温柔。
我的老家,虽然水脉纵横,可润泽的都是耕田牧羊的素淡人家,从没出一个李清照这样的灵秀人物,或男子,或女子。想来,两片土地的差距,就在那一汪泉水吧?于是,我常常遥望远方,想那泉水叮咚的样子,经年又经年。
三百里路,是17岁的少年第一次的人生长途。那年,我终于出发了,单车叮铃铃的铃声,一路向远……
故乡有荷也有柳。荷在水,柳在岸,荷凭水而美,柳舞风而媚。
夏日的校园,荷香悠悠,杨柳依依。在这里,少年的我,读到了那首《如梦令》。读了,就心生喜欢。想这写词的女子,笔下有荷,她那里,也必定有柳。那绿荫掩映的门楣,就是她的家。不远处,是让她醉而忘归的荷塘,那里鸥鸟翔集。
在我的意念里,李清照身似翠柳,心有荷香,梦如轻舟。后来,知晓她的老家就在济南的泉水边,也就更坚定了这种想法。甚至一度无来由地认为,柳泉居士的别号应属于李清照,而不是蒲松龄。想那说狐论妖的蒲老爷子,穷困潦倒,年高体衰,怎么能有这样柳新泉明的别号呢?太不相宜,太不相宜了。终究是,李清照的家,有柳亦有泉。柳色泉影,柳泉居士这别号,更适合这个宋朝的女子。清澈、飘逸、自在,多好!
为此,我臆想着如果有机会去往淄川,真希望能遇到那个在街头煮茶待客索故事的蒲老先生,和他说说这别号的事。我想,他一定会捋着胡子、笑着朝我点点头。当然,他也会舍我一杯茶,尽管我不会说鬼故事给他。那茶,可是柳叶茶么?反正他笔下的故事,大都似柳叶茶,苦而败火。
那时候,对于鬼妖我还是有所畏怕的,从同学家借来《聊斋志异》,也没怎么敢看。那书是竖排的繁体字,对我来说也的确读不扎实,再加上那泛黄的纸页,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所以很快就还了回去。即便如此,对于说鬼说妖的蒲松龄先生,却没有丝毫惧意,想来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毕竟我们村东头那个独居的本家爷爷,就常常用鬼怪的说词来逗弄我们,可他更愿意用他家树上结的各种果子来哄我们开心。
蒲松龄应该也是这样一个老头,惹人惊心,又让人欢喜。
明水,一听这名字,波光粼粼的,就感觉满是灵气,轻轻一念读,舌尖上就滑过丝绸般的柔爽。这个济南章丘的小镇,和诸多的小镇一样,既有城的富足和喧闹,也有村的朴实和忙碌,镶嵌在大片大片的田野中,像一块雕花的玉。相传,在明水有三处水量丰沛的泉眼,因为各在三户殷实人家,不为常人所见,所以被称“三不露”。其中一户就是李家,这李家,就是李清照的家。据说,她的名字就取自这泉水的波光闪烁。
上天的灵感,自是不同凡响。如此,这个出生于小镇的女孩,从小沐浴着清泉水般的宠爱,俨然就有了泉水一样活泼的灵魂,不拘教条;也就有了泉水一样清澈的才情,艳冠群芳。她的性格就像这小镇,亦城亦乡,既华贵,又泼辣。静,就守着泉眼出神,入痴入禅,像一朵荷;动,就追着泉水奔跑,翻沟越坎,像一缕风。
从青砖灰瓦的巷子里走出来,她一路成长。不远的田野里是大片的麦子,也有一丛丛杨柳、桃李或是桑林。那是一片悠游自在的天地。应当是就此成就了李清照的婉约与豪放。
当小小的她随着父亲来到东京汴梁,面对这个堆金叠玉的城,面对这个群英荟萃的城,没有丝毫胆怯。更是在名流云集的诗词场合,抑扬顿挫地张扬着自己,以称赞“梅定妒,菊应羞”的桂花为由头,暗喻自己“自是花中第一流”。可她遇了那个男子,又有了“和羞走”的温柔。
我的老家,虽然水脉纵横,可润泽的都是耕田牧羊的素淡人家,从没出一个李清照这样的灵秀人物,或男子,或女子。想来,两片土地的差距,就在那一汪泉水吧?于是,我常常遥望远方,想那泉水叮咚的样子,经年又经年。
三百里路,是17岁的少年第一次的人生长途。那年,我终于出发了,单车叮铃铃的铃声,一路向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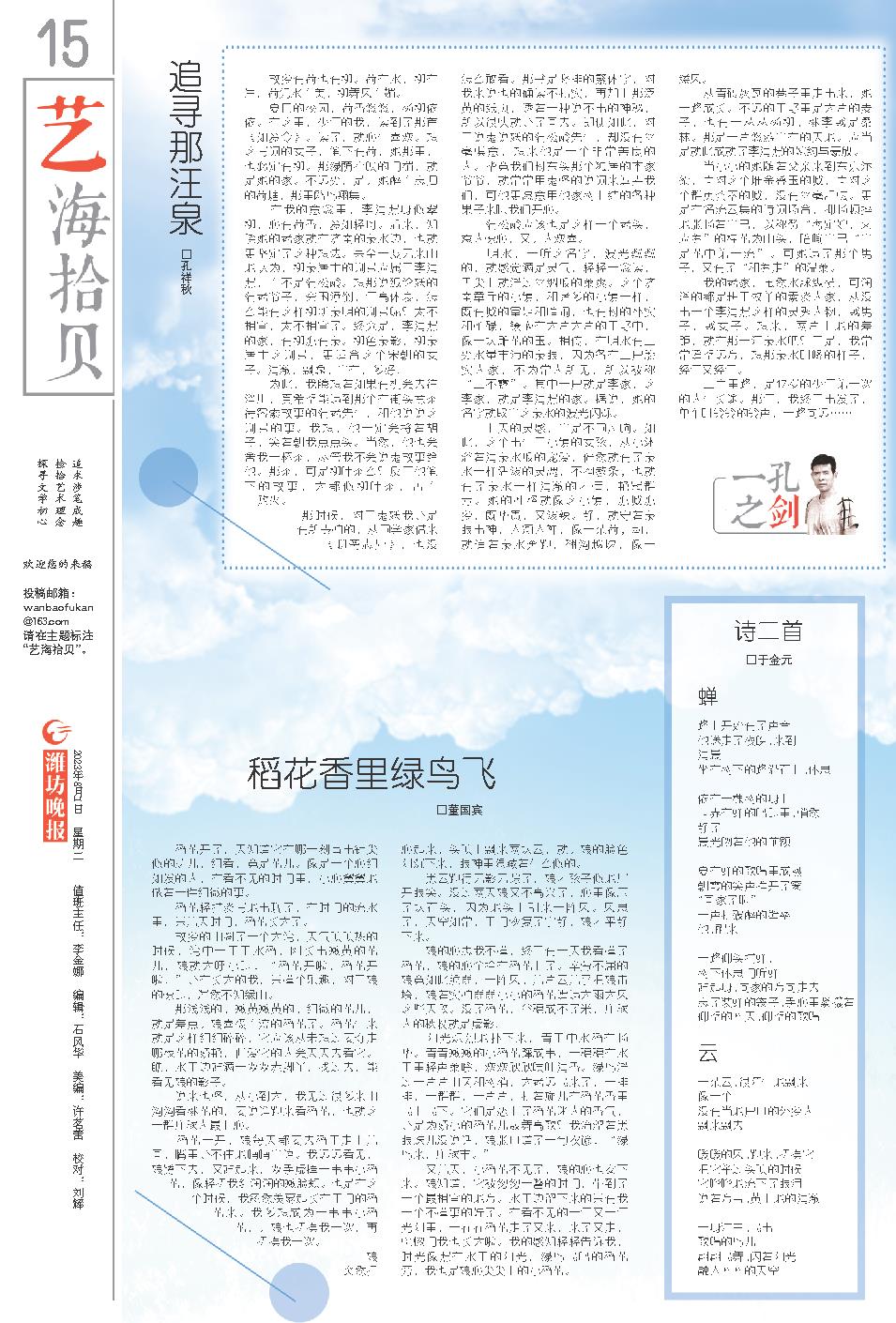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1/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