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版:文娱圈
10版:文娱圈
- * 围琴而坐 弦鸣清人心
- * 书画古琴雅韵和鸣
- * 多流派带来多体验
 13版:健康
13版:健康
- *
对付过敏性鼻炎
不妨试试这几招 - *
居家环境想健康
做好清洁很重要 - * 分类广告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灌溉进行时
□王觞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犹如探之不尽的宝藏。有些我们几乎天天与其见面,有的则几乎难见“真身”。
“攴”,就是一个几乎很难从当下出版物中看到“真身”的汉字。但是,它的“变身”却经常与我们面对面。
它是《说文》部首之一,读作pū。从属于这个部首的字有“教”“效”“政”“攻”“改”“败”“敲”“鼓”“收”“牧”“敌”“故”“数”“敛”“寇”等。其繁体字形亦然。
“攴”的甲骨文写作“ ”,象手持物击打之形。《说文解字》谓:“攴,小击也。”
“攴”字的小篆字形写作“ ”,它在楷书里面则是“一字化三形”,分别为“攴”“支”“攵”。
比如,在“敲”“寇”字中,它的字形为“攴”;而在“教”“效”“故”“政”等字中,它的字形为“攵”;在“鼓”字中,则变形为“支”。
作为一个部首,“攴”参与造字时,多表示不是非常酷烈地“击打”,更多时候含有“督促”之意。
比如,在“教”“牧”等字中,“攴”都可以理解为“督促”之意。
需要强调的是,“攵”与“文”二字毫无关系,今人仅仅因为其楷书字形相似,便给“攵”安了一个名字,把它叫做“反文旁”。
教育本是传播、传承文化的大事业,硬把“教”字的右侧部分称为“反文”,实在不妥。
当然,事无绝对。“攴”在参与造字时,虽然大多不表示酷烈的击打,但有些时候也表示用力比较猛的击打。
比如,“败”字即是一例。
“败”的甲骨文写作“ ”,象手持棍棒一类击鼎之形,由此引申出破坏等字义。这里的“攴”,显然不含“督促”一类的意思了。
再如,“政”字里面的“攴”,也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政”字的甲骨文写作“ ”,左上侧表示所去之地,左下侧为脚板之形,表示人的行动、行为;右侧则为“攴”。
《说文解字》谓:“政,正也。”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古人说的这个“正”字,看作使动用法,即“使(让)……正”。
《论语·颜渊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的意思大概是:你使(让)自己“正”,作出表率,谁还敢不正呢?
可以看得出来,“攴”在这里针对的对象为全部的施政对象。
在“寇”字里面,“攴”表达的意思也比较凶猛,毕竟是要把来犯之人赶出去、赶跑,所以也不同于“督促”这一类正面的含义。
通过对以上几个例字的分析,大家体会到我们祖先的脑洞有多大了吗?体会到古人思维的发散性有多么强烈了吗?
我们不妨打一个比方。古人在使用某个象形文字(比如攴)+其他部首(比如正、古、交等),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创造新文字时,这个选定的象形文字往往犹如一座山,有时候我们看到了山的正面,有时候则看到了山的侧面。一如苏东坡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当我们回到选定的象形文字本身时,它依然是那个“庐山”——其本身不变,变的是我们的视角。
如果我们把这个选定的象形文字称为“原点”,则我们考察据此创造的新文字时,必须要回到这个“原点”,站在“原点”上考察新文字,才更有利于思接千载、会意古人。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犹如探之不尽的宝藏。有些我们几乎天天与其见面,有的则几乎难见“真身”。
“攴”,就是一个几乎很难从当下出版物中看到“真身”的汉字。但是,它的“变身”却经常与我们面对面。
它是《说文》部首之一,读作pū。从属于这个部首的字有“教”“效”“政”“攻”“改”“败”“敲”“鼓”“收”“牧”“敌”“故”“数”“敛”“寇”等。其繁体字形亦然。
“攴”的甲骨文写作“ ”,象手持物击打之形。《说文解字》谓:“攴,小击也。”
“攴”字的小篆字形写作“ ”,它在楷书里面则是“一字化三形”,分别为“攴”“支”“攵”。
比如,在“敲”“寇”字中,它的字形为“攴”;而在“教”“效”“故”“政”等字中,它的字形为“攵”;在“鼓”字中,则变形为“支”。
作为一个部首,“攴”参与造字时,多表示不是非常酷烈地“击打”,更多时候含有“督促”之意。
比如,在“教”“牧”等字中,“攴”都可以理解为“督促”之意。
需要强调的是,“攵”与“文”二字毫无关系,今人仅仅因为其楷书字形相似,便给“攵”安了一个名字,把它叫做“反文旁”。
教育本是传播、传承文化的大事业,硬把“教”字的右侧部分称为“反文”,实在不妥。
当然,事无绝对。“攴”在参与造字时,虽然大多不表示酷烈的击打,但有些时候也表示用力比较猛的击打。
比如,“败”字即是一例。
“败”的甲骨文写作“ ”,象手持棍棒一类击鼎之形,由此引申出破坏等字义。这里的“攴”,显然不含“督促”一类的意思了。
再如,“政”字里面的“攴”,也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政”字的甲骨文写作“ ”,左上侧表示所去之地,左下侧为脚板之形,表示人的行动、行为;右侧则为“攴”。
《说文解字》谓:“政,正也。”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古人说的这个“正”字,看作使动用法,即“使(让)……正”。
《论语·颜渊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的意思大概是:你使(让)自己“正”,作出表率,谁还敢不正呢?
可以看得出来,“攴”在这里针对的对象为全部的施政对象。
在“寇”字里面,“攴”表达的意思也比较凶猛,毕竟是要把来犯之人赶出去、赶跑,所以也不同于“督促”这一类正面的含义。
通过对以上几个例字的分析,大家体会到我们祖先的脑洞有多大了吗?体会到古人思维的发散性有多么强烈了吗?
我们不妨打一个比方。古人在使用某个象形文字(比如攴)+其他部首(比如正、古、交等),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创造新文字时,这个选定的象形文字往往犹如一座山,有时候我们看到了山的正面,有时候则看到了山的侧面。一如苏东坡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当我们回到选定的象形文字本身时,它依然是那个“庐山”——其本身不变,变的是我们的视角。
如果我们把这个选定的象形文字称为“原点”,则我们考察据此创造的新文字时,必须要回到这个“原点”,站在“原点”上考察新文字,才更有利于思接千载、会意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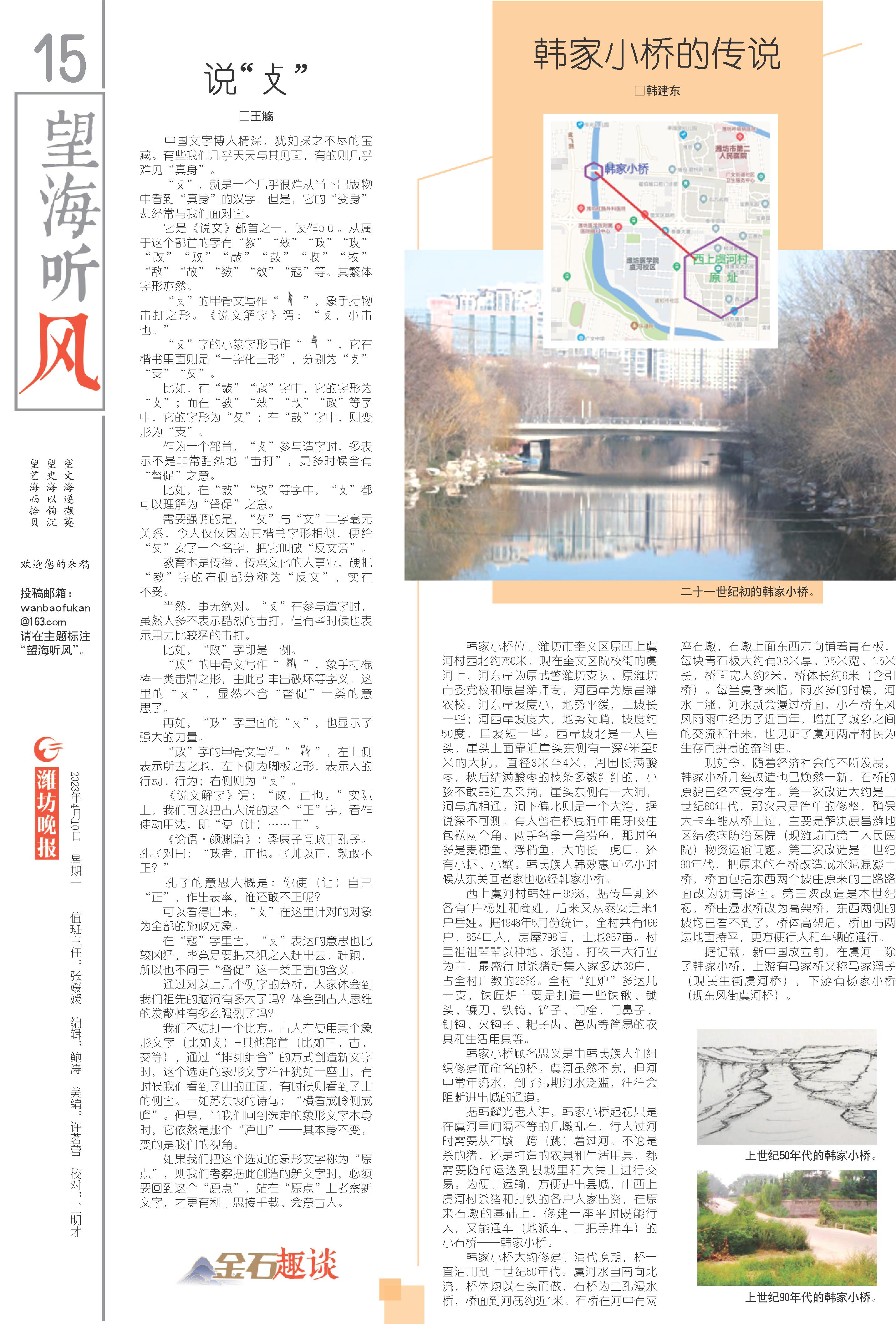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10/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