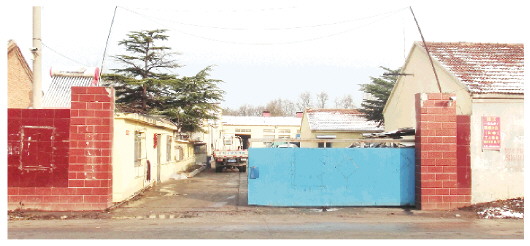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粽香里品中国味
 04版:潍坊人物
04版:潍坊人物
- * 用专业和温情助更多家庭“好孕”
- * 名医小档案
 08版:光影记录
08版:光影记录
- * 在路上
 09版:人文潍坊
09版:人文潍坊
- * 难以忘却的记忆
为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潍县建立了公社铁木厂。师徒搭档走向田边,服务到家。高里公社创办了农业技术中学,毕业生只有两届,在学校的推荐下,进了公社铁木厂、水利站等地工作。潍坊市集中下放了一批特困户,于明一家在双杨公社后阙庄大队落户,在不少下放户一心要回城的时候,于明一家却在农村扎下根来。
铁木厂工人造修农具 服务于田头沟边
1958年“大跃进”前夕,为适应形势,潍县把相连片区的初高级社多个铁木社合并组成了“公社铁木厂”,开始前所未有的规模化生产,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双杨公社铁木厂因时成立,设有钳工、木工、红炉等车间或班组,聘请散落民间的老工人当师傅,招收满18岁、体格强壮、愿意出力的年轻人当学员。但铁木厂成立不久,有的学员便听闻东北、西北工资更高,“外流”了。
铁木厂的红炉分外忙碌,对锄、镰、锨、镢这些传统农具不是修理淬火,就是新打现制。
铁木厂工人直接下村当支农“轻骑兵”,一师一徒搭档,推起小车,担上煤炭,“叮当”在田头沟边上,吃喝在太阳月亮下。厂里没规定非下到哪个村,只要求不留服务死角。有的搭档曾到十几里远的地方,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没人叫苦,没人打退堂鼓。回厂的夜路上,就掐算明天再到哪里去。收到的服务费,都是凭“三联单”一分不少地上缴财会室。
1962年10月,国家为恢复国民经济,停办铁木厂一年;次年恢复时,有的工人竟不回来了,理由是收入太低。
最早进双杨公社铁木厂学徒,一直干到副厂长的张希尚,现在退休金3000多元,叫许多半路而退的人眼馋,说他“好命”。张希尚则认为是自己咬牙坚持的结果。1971年7月工资微调前,他的工资才每月29元,每年都要买工分养家糊口。老婆有病,回家就有干不完的农活。可一想到当红炉工的39斤口粮,曾帮助家里渡过了难关,便很知足,很感激。他说:“命运不是天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1983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公社解体,铁木厂淡出至消失,大约存在了30年。它不能与现代化工厂相比,但它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工人们吃苦耐劳、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的“铁木厂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张希尚口述
农技中实行免费制度 毕业生跳出农门
1959年,在官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双轨并行的“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指引下,高里公社创办农业技术中学(以下简称农技中),实行县社双重领导和免费制度,从小学毕业生中招生。最初两个班60余人,三年后毕业;1962年,经济开始好转,就能年年招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停招,不久学校撤销。
农技中的课本、课程基本和普通初中一样,只是增加了生物课(植物、动物),每周节数;还有手工劳动课,以及“农业八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宪法”自读讲义。校长先后由公社社长李功盛和公社文教助理魏金声兼任;教师多数从正式学校聘来兼职,个别自高中毕业生中招聘。
学生每周回家一次,自带干粮、面子和咸菜。课桌是菱苦土材质的,坐具自带。一个几乎捏不住的粉笔头,老师都舍不得丢;作业本是4分钱一张的白纸剪钉的,正反两面都写得密密麻麻……学生们很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遇到难处,没人气馁,校园中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氛围。
相比普通初中生,农技中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开辟“社会大课堂”,外出参观了不少地方,增加感性认识,坚定了学习信心。
到1965年,有两届毕业生。家长最关心他们的去向,都希望孩子能“跳出农门”。虽然没有政策支持分配,但学校也尽量推荐、安排。有的学生进了公社铁木厂、水利站、农机站、供销社,有的当了民办教师、大队会计、卫生员等。学生们都感到没有白学。
张树生口述
下放特困户于明 扎根农村无怨无悔
1964年10月1日,潍坊市集中下放了一批特困户。于明一家和另外七户来到潍县双杨公社后阙庄大队,分别安排在“五保户”空房或人少屋多的主家。房东们很热情,很快就不生分了。社员们手把手地教他们怎么干活,“沉脏累”暂不安排,同工同酬。第二年分细粮小麦,社员人均46斤,下放户却分得80斤。不到两年,下放户都有了“产权”属于自己的3到5间瓦檐屋,天井又大又宽敞。有技术专长的进了公社铁木厂,立马带徒弟;安心干农活的,有的当了生产队长,有的成了社员骨干。入党、入团、入伍的待遇与贫下中农一样。
于明一家也是下放户,鉴于父亲有腿疾,15岁的于明在本村小学一毕业,就顶整劳力干活了。他不怕脏累,性格合群,得到社员一致好评。有的下放户却不记当初受到的优待,认为下乡成了“单门独户”“屈才”“受欺负”,不安心生产,要求返城。他们经常凑在于明家里闲聊,散布有关下放户的负面消息。村里后来有了青岛来的知识青年,也经常和于明走动,其中也不乏回城言论。于明家有台收音机,1971年10月26日,播出了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新闻,于明趁机说:“地球上哪个国家也是‘单门独户’吧?一个国家自强自立了,国际大家庭就会接纳它、对它友好、高看它。大国小家一个理,首先要内心强大,不妄自菲薄,然后再去实干。”大家听了,先是哑口无言,稍后鼓起了掌……
1983年,潍坊市政府下达了1964年下放户全部回城的决定。那时,于明已娶了本村媳妇10年了,已当了十队队长5年多,妹妹也由他做媒嫁给本村人。对于回城,他却高兴不起来。村支书风趣地说:“你能挣断九头牛拉你的绳子,我就放你走!”于明感到这么受信任,更要留乡了。在农村待了一辈子,他无怨无悔,没高调讲大道理,只是说:“现在‘城乡差别’越来越小,农村住房宽敞,自种菜粮更放心,空气新鲜,开车不堵少碰撞,有不少超市很方便……”
于明口述
铁木厂工人造修农具 服务于田头沟边
1958年“大跃进”前夕,为适应形势,潍县把相连片区的初高级社多个铁木社合并组成了“公社铁木厂”,开始前所未有的规模化生产,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双杨公社铁木厂因时成立,设有钳工、木工、红炉等车间或班组,聘请散落民间的老工人当师傅,招收满18岁、体格强壮、愿意出力的年轻人当学员。但铁木厂成立不久,有的学员便听闻东北、西北工资更高,“外流”了。
铁木厂的红炉分外忙碌,对锄、镰、锨、镢这些传统农具不是修理淬火,就是新打现制。
铁木厂工人直接下村当支农“轻骑兵”,一师一徒搭档,推起小车,担上煤炭,“叮当”在田头沟边上,吃喝在太阳月亮下。厂里没规定非下到哪个村,只要求不留服务死角。有的搭档曾到十几里远的地方,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没人叫苦,没人打退堂鼓。回厂的夜路上,就掐算明天再到哪里去。收到的服务费,都是凭“三联单”一分不少地上缴财会室。
1962年10月,国家为恢复国民经济,停办铁木厂一年;次年恢复时,有的工人竟不回来了,理由是收入太低。
最早进双杨公社铁木厂学徒,一直干到副厂长的张希尚,现在退休金3000多元,叫许多半路而退的人眼馋,说他“好命”。张希尚则认为是自己咬牙坚持的结果。1971年7月工资微调前,他的工资才每月29元,每年都要买工分养家糊口。老婆有病,回家就有干不完的农活。可一想到当红炉工的39斤口粮,曾帮助家里渡过了难关,便很知足,很感激。他说:“命运不是天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1983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公社解体,铁木厂淡出至消失,大约存在了30年。它不能与现代化工厂相比,但它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工人们吃苦耐劳、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的“铁木厂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张希尚口述
农技中实行免费制度 毕业生跳出农门
1959年,在官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双轨并行的“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指引下,高里公社创办农业技术中学(以下简称农技中),实行县社双重领导和免费制度,从小学毕业生中招生。最初两个班60余人,三年后毕业;1962年,经济开始好转,就能年年招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停招,不久学校撤销。
农技中的课本、课程基本和普通初中一样,只是增加了生物课(植物、动物),每周节数;还有手工劳动课,以及“农业八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宪法”自读讲义。校长先后由公社社长李功盛和公社文教助理魏金声兼任;教师多数从正式学校聘来兼职,个别自高中毕业生中招聘。
学生每周回家一次,自带干粮、面子和咸菜。课桌是菱苦土材质的,坐具自带。一个几乎捏不住的粉笔头,老师都舍不得丢;作业本是4分钱一张的白纸剪钉的,正反两面都写得密密麻麻……学生们很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遇到难处,没人气馁,校园中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氛围。
相比普通初中生,农技中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开辟“社会大课堂”,外出参观了不少地方,增加感性认识,坚定了学习信心。
到1965年,有两届毕业生。家长最关心他们的去向,都希望孩子能“跳出农门”。虽然没有政策支持分配,但学校也尽量推荐、安排。有的学生进了公社铁木厂、水利站、农机站、供销社,有的当了民办教师、大队会计、卫生员等。学生们都感到没有白学。
张树生口述
下放特困户于明 扎根农村无怨无悔
1964年10月1日,潍坊市集中下放了一批特困户。于明一家和另外七户来到潍县双杨公社后阙庄大队,分别安排在“五保户”空房或人少屋多的主家。房东们很热情,很快就不生分了。社员们手把手地教他们怎么干活,“沉脏累”暂不安排,同工同酬。第二年分细粮小麦,社员人均46斤,下放户却分得80斤。不到两年,下放户都有了“产权”属于自己的3到5间瓦檐屋,天井又大又宽敞。有技术专长的进了公社铁木厂,立马带徒弟;安心干农活的,有的当了生产队长,有的成了社员骨干。入党、入团、入伍的待遇与贫下中农一样。
于明一家也是下放户,鉴于父亲有腿疾,15岁的于明在本村小学一毕业,就顶整劳力干活了。他不怕脏累,性格合群,得到社员一致好评。有的下放户却不记当初受到的优待,认为下乡成了“单门独户”“屈才”“受欺负”,不安心生产,要求返城。他们经常凑在于明家里闲聊,散布有关下放户的负面消息。村里后来有了青岛来的知识青年,也经常和于明走动,其中也不乏回城言论。于明家有台收音机,1971年10月26日,播出了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新闻,于明趁机说:“地球上哪个国家也是‘单门独户’吧?一个国家自强自立了,国际大家庭就会接纳它、对它友好、高看它。大国小家一个理,首先要内心强大,不妄自菲薄,然后再去实干。”大家听了,先是哑口无言,稍后鼓起了掌……
1983年,潍坊市政府下达了1964年下放户全部回城的决定。那时,于明已娶了本村媳妇10年了,已当了十队队长5年多,妹妹也由他做媒嫁给本村人。对于回城,他却高兴不起来。村支书风趣地说:“你能挣断九头牛拉你的绳子,我就放你走!”于明感到这么受信任,更要留乡了。在农村待了一辈子,他无怨无悔,没高调讲大道理,只是说:“现在‘城乡差别’越来越小,农村住房宽敞,自种菜粮更放心,空气新鲜,开车不堵少碰撞,有不少超市很方便……”
于明口述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23/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