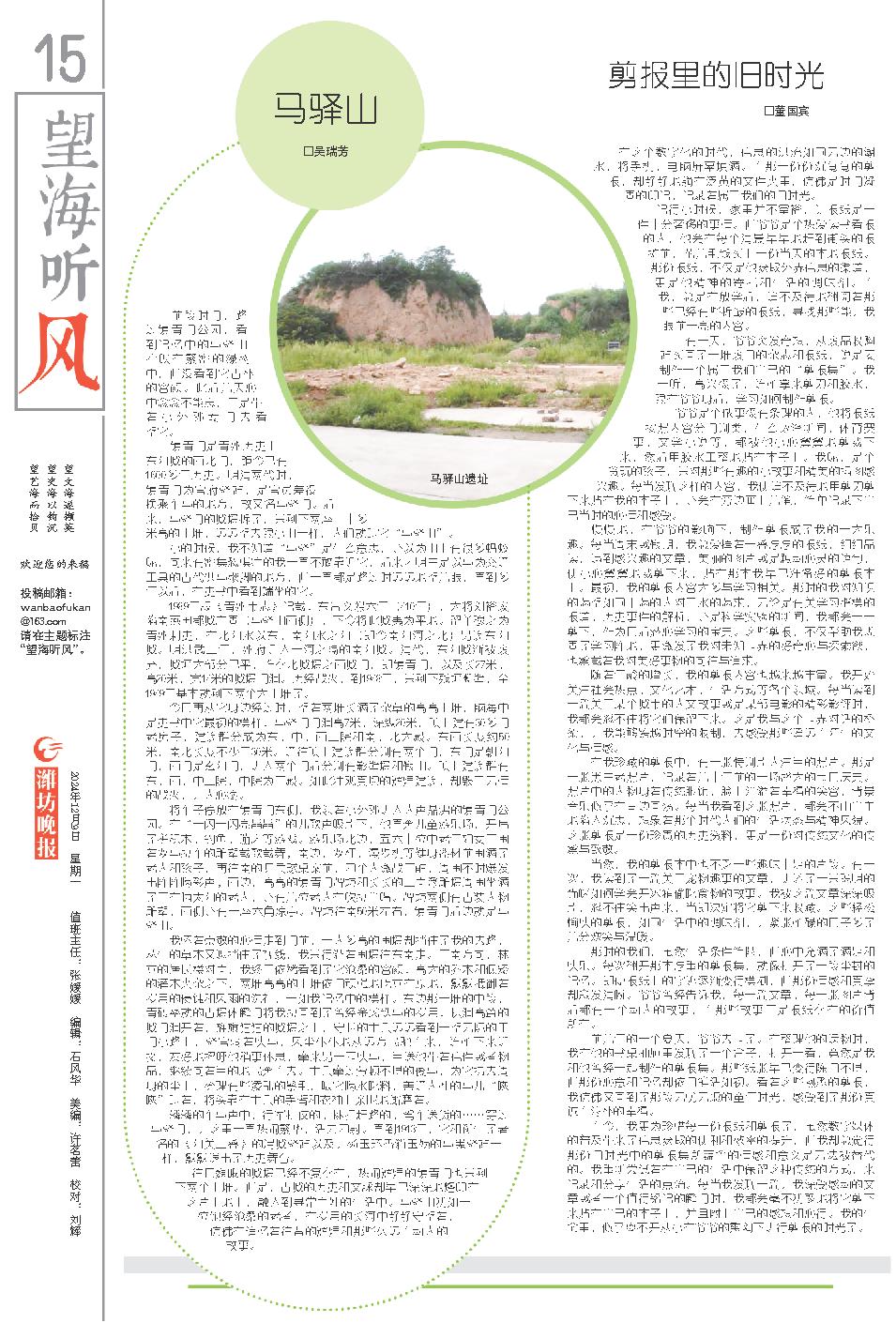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谁羽争锋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礼赞
□吴瑞芳
前段时间,路过镇青门公园,看到记忆中的马驿山掩映在繁密的绿树中,但没看到它古朴的容颜。此后几天心中念念不能忘,于是带着小外孙专门去看望它。
镇青门是青州历史上东阳城的西北门,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明清两代时,镇青门为官府驿站,是官员差役换乘车马的地方,故又名马驿门。后来,马驿门的城墙拆了,只剩下两座二十多米高的土堆,远远望去跟小山一样,人们就叫它“马驿山”。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马驿”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山上有很多蚂蚁呢,向来有密集恐惧症的我一直不敢靠近它,后来才明白是以马为交通工具的古代供马歇脚的地方,但一直都是路过时远远地望几眼,直到多年以后,在史书中看到端坐的它。
1989年版《青州市志》记载: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大将刘裕攻陷南燕国都城广固(马驿山西侧),下令将此城夷为平地。留羊穆之为青州刺史,在北阳水以东、南阳水之阳(即今南阳河之北)另筑东阳城。明洪武三年,州府迁入一河之隔的南阳城。清代,东阳城渐被废弃,城垣大部分已平,唯存北城墙之西城门,即镇青门,以及长27米、高20米、宽14米的城墙门洞。历经战火,到1948年,只剩下残垣断壁,至1949年基本就剩下两个大土堆了。
今日再从它身边经过时,望着两堆长满了杂草的高高土堆,脑海中是史书中它最初的模样:马驿门门洞高7米、深纵20米,顶上建有30多间老房子,建筑群分成为东、中、西三院和南、北大殿。东西长度约50米,南北长度不少于30米。通往顶上建筑群分别有两个门,东门是朝阳门,西门是玄阳门,进入两个门后分别有影壁墙和假山。顶上建筑群有东、西、中三院,中院为正殿。如此壮观真切的辉煌建筑,却毁于无情的战火,让人心疼。
将车子停放在镇青门东侧,我领着小外孙进入人声鼎沸的镇青门公园。在“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儿歌声吸引下,他直奔儿童游乐场,开启了拼积木、钓鱼、蹦床等游戏。游乐场北边,五六十位中老年妇女正围着双马拉车的雕塑载歌载舞;南边,双杠、漫步机等健身器材前围满了老人和孩子,再往南的乒乓球桌案前,四个人激战正酣,周围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声;西边,高高的镇青门牌坊和长长的三面浮雕墙周围坐满了正在晒太阳的老人,还有几位老人在吹拉弹唱。牌坊两侧有古装人物雕塑,西侧还有一座六角凉亭。牌坊往南50米左右,镇青门后边就是马驿山。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门前,一人多高的围墙却挡住了我的去路,丛生的草木又遮挡住了视线,我只得沿着围墙往东南走。正南方向,林立的居民楼对面,我终于依稀看到了它沧桑的容颜:高大的乔木和低矮的灌木夹杂之下,两堆高高的土堆依旧顽强地屹立在原地,默默抵御着岁月的侵蚀和风雨的洗礼,一如我记忆中的模样。东边那一堆的中段,青砖垒就的古墙体瞬间将我拉回到了曾经金戈铁马的岁月:拱洞高耸的城门洞开着,旌旗猎猎的城墙之上,守卫的士兵远远看到一望无际的田间小路上,驿官骑着快马,风尘仆仆地从远方飞驰而来,连忙下来迎接,友好地招呼他稍事休息,牵来另一匹快马,目送他带着信件或者物品,继续向着目的地飞奔而去。士兵牵过劳顿不堪的俊马,为它拂去周身的尘土,梳理有些凌乱的鬃毛,喂它喝水吃料,善通人性的马儿“咴咴”叫着,将头靠在士兵的手臂和衣袖上亲昵地厮磨着。
辚辚的车马声中,行军打仗的、挑担赶路的、驾车送货的……穿过马驿门,让这里一直热闹繁华、活力四射。直到1913年,它和诞生了著名的《阳关三叠》的渭城驿站以及让杨玉环香消玉殒的马嵬驿站一样,默默退出了历史舞台。
往日巍峨的城墙已经不复存在,热闹辉煌的镇青门也只剩下两个土堆。但是,古城的历史和文脉却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融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马驿山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守望着,仿佛在追忆着往昔的辉煌和那些久远而动人的故事。
前段时间,路过镇青门公园,看到记忆中的马驿山掩映在繁密的绿树中,但没看到它古朴的容颜。此后几天心中念念不能忘,于是带着小外孙专门去看望它。
镇青门是青州历史上东阳城的西北门,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明清两代时,镇青门为官府驿站,是官员差役换乘车马的地方,故又名马驿门。后来,马驿门的城墙拆了,只剩下两座二十多米高的土堆,远远望去跟小山一样,人们就叫它“马驿山”。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马驿”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山上有很多蚂蚁呢,向来有密集恐惧症的我一直不敢靠近它,后来才明白是以马为交通工具的古代供马歇脚的地方,但一直都是路过时远远地望几眼,直到多年以后,在史书中看到端坐的它。
1989年版《青州市志》记载: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大将刘裕攻陷南燕国都城广固(马驿山西侧),下令将此城夷为平地。留羊穆之为青州刺史,在北阳水以东、南阳水之阳(即今南阳河之北)另筑东阳城。明洪武三年,州府迁入一河之隔的南阳城。清代,东阳城渐被废弃,城垣大部分已平,唯存北城墙之西城门,即镇青门,以及长27米、高20米、宽14米的城墙门洞。历经战火,到1948年,只剩下残垣断壁,至1949年基本就剩下两个大土堆了。
今日再从它身边经过时,望着两堆长满了杂草的高高土堆,脑海中是史书中它最初的模样:马驿门门洞高7米、深纵20米,顶上建有30多间老房子,建筑群分成为东、中、西三院和南、北大殿。东西长度约50米,南北长度不少于30米。通往顶上建筑群分别有两个门,东门是朝阳门,西门是玄阳门,进入两个门后分别有影壁墙和假山。顶上建筑群有东、西、中三院,中院为正殿。如此壮观真切的辉煌建筑,却毁于无情的战火,让人心疼。
将车子停放在镇青门东侧,我领着小外孙进入人声鼎沸的镇青门公园。在“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儿歌声吸引下,他直奔儿童游乐场,开启了拼积木、钓鱼、蹦床等游戏。游乐场北边,五六十位中老年妇女正围着双马拉车的雕塑载歌载舞;南边,双杠、漫步机等健身器材前围满了老人和孩子,再往南的乒乓球桌案前,四个人激战正酣,周围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声;西边,高高的镇青门牌坊和长长的三面浮雕墙周围坐满了正在晒太阳的老人,还有几位老人在吹拉弹唱。牌坊两侧有古装人物雕塑,西侧还有一座六角凉亭。牌坊往南50米左右,镇青门后边就是马驿山。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门前,一人多高的围墙却挡住了我的去路,丛生的草木又遮挡住了视线,我只得沿着围墙往东南走。正南方向,林立的居民楼对面,我终于依稀看到了它沧桑的容颜:高大的乔木和低矮的灌木夹杂之下,两堆高高的土堆依旧顽强地屹立在原地,默默抵御着岁月的侵蚀和风雨的洗礼,一如我记忆中的模样。东边那一堆的中段,青砖垒就的古墙体瞬间将我拉回到了曾经金戈铁马的岁月:拱洞高耸的城门洞开着,旌旗猎猎的城墙之上,守卫的士兵远远看到一望无际的田间小路上,驿官骑着快马,风尘仆仆地从远方飞驰而来,连忙下来迎接,友好地招呼他稍事休息,牵来另一匹快马,目送他带着信件或者物品,继续向着目的地飞奔而去。士兵牵过劳顿不堪的俊马,为它拂去周身的尘土,梳理有些凌乱的鬃毛,喂它喝水吃料,善通人性的马儿“咴咴”叫着,将头靠在士兵的手臂和衣袖上亲昵地厮磨着。
辚辚的车马声中,行军打仗的、挑担赶路的、驾车送货的……穿过马驿门,让这里一直热闹繁华、活力四射。直到1913年,它和诞生了著名的《阳关三叠》的渭城驿站以及让杨玉环香消玉殒的马嵬驿站一样,默默退出了历史舞台。
往日巍峨的城墙已经不复存在,热闹辉煌的镇青门也只剩下两个土堆。但是,古城的历史和文脉却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融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马驿山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守望着,仿佛在追忆着往昔的辉煌和那些久远而动人的故事。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09/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