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金龙飞天
红火迎年
 15版:艺海拾贝
15版:艺海拾贝
- * 去梅开的南方等一场大雪
- * 冬日之歌 傍晚鸟鸣
- *
月夜
我走进雪地 - * 感谢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雪后的村庄
□孔祥秋
窗外,又飘起了雪花。这时候说梅花,似乎最适宜。
踏雪寻梅,古人的风雅传奇,意境真是妙。就在这样的雪天,或自己,或三两好友,慢慢游走,在下一个转角处,忽然就有一枝梅花旁逸斜出,真好。雪,不可太厚,也不可太薄。路,最好是山路,曲曲折折的最好,若是太直,就少了情趣。
在北方的冬天,雪是不缺的,但红梅却多生南方,而南方又少有雪天,如此踏雪寻梅这样的事,也就可遇不可求了。当然,有人说在北方踏雪寻的梅是蜡梅。蜡梅,在北方是常见的,如此雪中相寻就容易多了。蜡梅,也天生丽质,不乏精神,但我认为还是雪中寻梅花更好。梅是那红梅,与雪的白正好相映出彩。
南方,多出文人雅士,诸多事物在笔墨下也就风雅无边,想那一个雨打芭蕉,就可以述说成喜怒哀乐的种种调子。就算南北都有的荷花,北方多注重水下之藕瓜,入了盘入了碗,南方则多着眼水上花与莲蓬,入了诗入了画。按说那“岁寒三友”应该是指北方的草木吧?可那竹、那梅,不是依然侧重于南方吗?也别怪南方人太解风情,善于文字渲染,那里的确有太多让人喜爱的风物,想我一直念叨的梅花,就是。
梅花说不上高与壮,与北方人的情感应该是不契合的,可它弯曲的枝干却如筋如铁,绝不是阿谀奉承的形态。而或蕾或朵的花,更像是绽开的火星。这样的精气神儿,再立于一场大雪之中,任谁不喜欢?
说实话,我是没有真正见过梅花的,尤其是雪中的梅花。树木,我都喜欢,特别是老家房前屋后的那些,它们,都那么富有智慧。想那杨树榆树这样的料材之木,就向高向壮;想那桃树梨树这样的果实之木,就枝丫横斜,宜花宜果。这多像乡间里那传统的品德,耕田的耕田,织布的织布,各专所长,各尽所能。那时候我喜欢画画,没想到第一笔画下的不是这些亲情般的树木,却是一抹初相见的花枝。
记得那年春节,姨父从外地回来探亲,我家的桌子上多了一盒烟。烟盒上是一枝花,黑的干,红的朵,好喜气。
从那,我知道了有一种花叫红梅,像极了屋门口的春联和福字,是可以迎春的。这花,让我喜欢。我就平平整整地将那烟盒纸展铺在灶台上,认认真真地临摹那梅花。
没经过沧桑,怎么能画得出那梅的枝;没见过风雨,哪能画得出那梅的朵?再说那油腻的蜡笔也实在不适合画梅花,可我依然乐此不疲,一张一张地画,一张一张地贴在炕头的墙上。那年回老家,老屋里竟然还有一张那时的画,从那隐隐约约的黑和隐隐约约的红里,看出那正是画的梅,丑丑的,哪有一点梅的样子?但我还是原谅了自己小时候的幼稚,谁没有这样的童真呢?
早些年,在县城一文化单位打工,办公室里常有远远近近的书画名家来往。文化人多在性情之中,几句言谈入了心,就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成了画案,那些书画家就调了颜料,展了纸张,一通才华纵横,就写了风月、画了山水。单位的人纷纷叫好,一一上前相求。这样的场面我是和大家一起欢喜的,也一样赞叹书画家的技艺,可我从来没有求过一幅字画。其实,我心里一直渴望一幅画,但直到我离开那里,也没等来一个画梅的人。
不是王者,不宣誓言,没有横刀立马的形影,梅,却以一种铮铮之气最宜入画。横入画框,可让人展胸襟;竖在卷轴,可让人立壮志。山寒水瘦又如何,梅就这样卷土重来,重整岁月待春风。一花作引领,一花作导航,所谓的穷途末路都不过是庸人自扰。
如此半生,若只是画里求梅,难免惹下叶公好龙的诟病。我想去南方,在梅开的南方,等一场大雪,让那雪中的梅,真正给我一种精神。只是近来身体欠佳,不知能否成行?
窗外,又飘起了雪花。这时候说梅花,似乎最适宜。
踏雪寻梅,古人的风雅传奇,意境真是妙。就在这样的雪天,或自己,或三两好友,慢慢游走,在下一个转角处,忽然就有一枝梅花旁逸斜出,真好。雪,不可太厚,也不可太薄。路,最好是山路,曲曲折折的最好,若是太直,就少了情趣。
在北方的冬天,雪是不缺的,但红梅却多生南方,而南方又少有雪天,如此踏雪寻梅这样的事,也就可遇不可求了。当然,有人说在北方踏雪寻的梅是蜡梅。蜡梅,在北方是常见的,如此雪中相寻就容易多了。蜡梅,也天生丽质,不乏精神,但我认为还是雪中寻梅花更好。梅是那红梅,与雪的白正好相映出彩。
南方,多出文人雅士,诸多事物在笔墨下也就风雅无边,想那一个雨打芭蕉,就可以述说成喜怒哀乐的种种调子。就算南北都有的荷花,北方多注重水下之藕瓜,入了盘入了碗,南方则多着眼水上花与莲蓬,入了诗入了画。按说那“岁寒三友”应该是指北方的草木吧?可那竹、那梅,不是依然侧重于南方吗?也别怪南方人太解风情,善于文字渲染,那里的确有太多让人喜爱的风物,想我一直念叨的梅花,就是。
梅花说不上高与壮,与北方人的情感应该是不契合的,可它弯曲的枝干却如筋如铁,绝不是阿谀奉承的形态。而或蕾或朵的花,更像是绽开的火星。这样的精气神儿,再立于一场大雪之中,任谁不喜欢?
说实话,我是没有真正见过梅花的,尤其是雪中的梅花。树木,我都喜欢,特别是老家房前屋后的那些,它们,都那么富有智慧。想那杨树榆树这样的料材之木,就向高向壮;想那桃树梨树这样的果实之木,就枝丫横斜,宜花宜果。这多像乡间里那传统的品德,耕田的耕田,织布的织布,各专所长,各尽所能。那时候我喜欢画画,没想到第一笔画下的不是这些亲情般的树木,却是一抹初相见的花枝。
记得那年春节,姨父从外地回来探亲,我家的桌子上多了一盒烟。烟盒上是一枝花,黑的干,红的朵,好喜气。
从那,我知道了有一种花叫红梅,像极了屋门口的春联和福字,是可以迎春的。这花,让我喜欢。我就平平整整地将那烟盒纸展铺在灶台上,认认真真地临摹那梅花。
没经过沧桑,怎么能画得出那梅的枝;没见过风雨,哪能画得出那梅的朵?再说那油腻的蜡笔也实在不适合画梅花,可我依然乐此不疲,一张一张地画,一张一张地贴在炕头的墙上。那年回老家,老屋里竟然还有一张那时的画,从那隐隐约约的黑和隐隐约约的红里,看出那正是画的梅,丑丑的,哪有一点梅的样子?但我还是原谅了自己小时候的幼稚,谁没有这样的童真呢?
早些年,在县城一文化单位打工,办公室里常有远远近近的书画名家来往。文化人多在性情之中,几句言谈入了心,就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成了画案,那些书画家就调了颜料,展了纸张,一通才华纵横,就写了风月、画了山水。单位的人纷纷叫好,一一上前相求。这样的场面我是和大家一起欢喜的,也一样赞叹书画家的技艺,可我从来没有求过一幅字画。其实,我心里一直渴望一幅画,但直到我离开那里,也没等来一个画梅的人。
不是王者,不宣誓言,没有横刀立马的形影,梅,却以一种铮铮之气最宜入画。横入画框,可让人展胸襟;竖在卷轴,可让人立壮志。山寒水瘦又如何,梅就这样卷土重来,重整岁月待春风。一花作引领,一花作导航,所谓的穷途末路都不过是庸人自扰。
如此半生,若只是画里求梅,难免惹下叶公好龙的诟病。我想去南方,在梅开的南方,等一场大雪,让那雪中的梅,真正给我一种精神。只是近来身体欠佳,不知能否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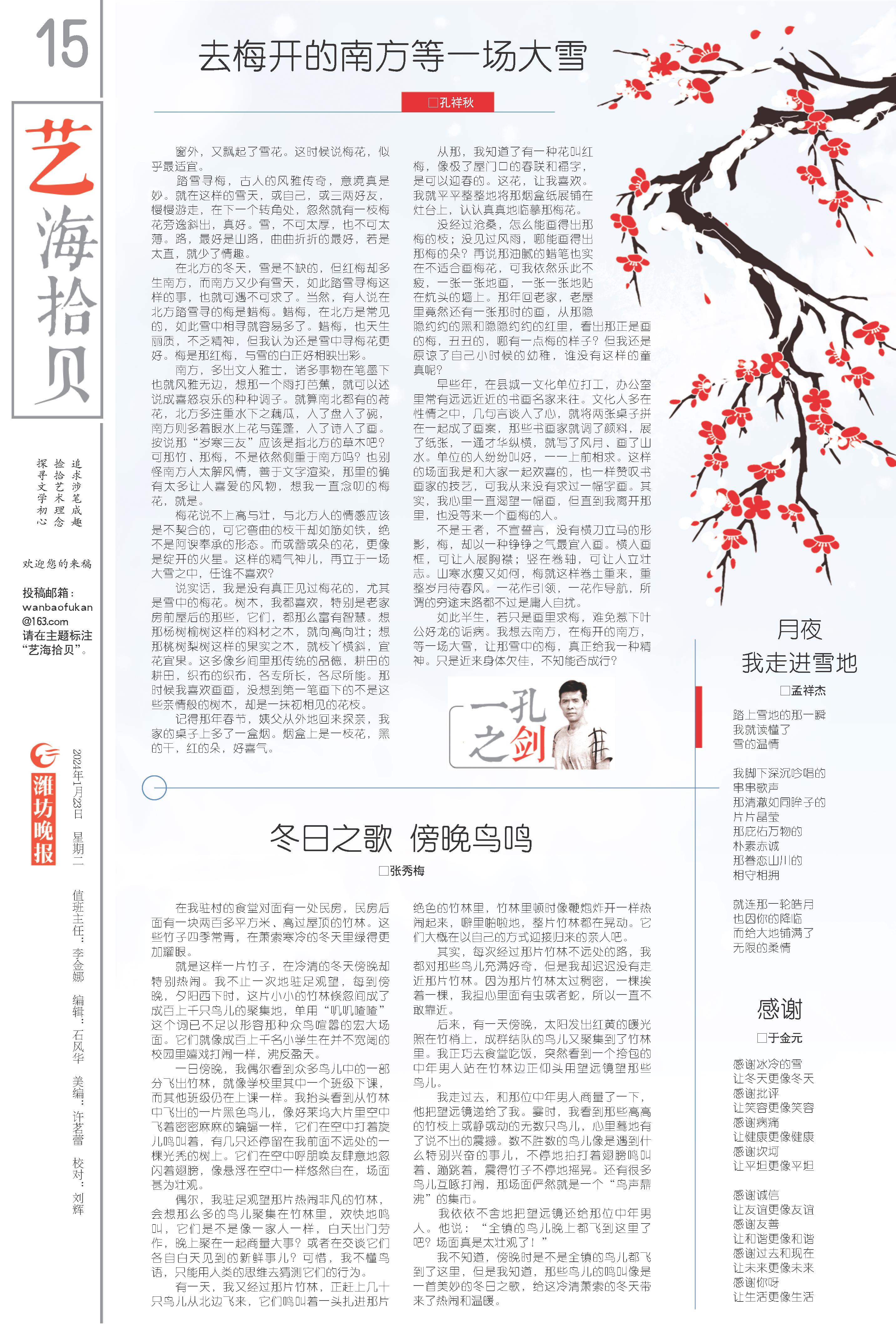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123/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