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图书馆遇上剧本杀
 11版:运动吧
11版:运动吧
- * 不再拥有高水准而急流勇退
- * 齐鲁棋院临朐培训基地成立
- * “家门口”参加篮球赛
- * 小运动员逐梦绿茵场
 15版:望海听风
15版:望海听风
- * 关于蒺藜的那些故事
- * 刘喜海与林则徐的交往
- * 说说人间四月天
□白芸
有些植物,因其特殊的生理属性和生长习性,注定要与人类产生密切的联系,碰撞出更多的精彩故事。比如,蒺藜。
把它藏进谜语里
植物被编进谜语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棵草,四下里跑,开黄花,结‘哎哟儿’”,这就是我老家的人为蒺藜量身打造的谜语。蒺藜会匍匐攀爬,花为黄色。“跑”,是指它以根基为圆心,努力扩大半径往外生长的蓬勃状态。“哎哟”,本是人被蒺藜刺扎时的一个本能反应,并非对植物特性的直接描述,但乡里人的语言总是那么切中要点,直接把这声惊叫具化为一个果实的样子。
还有谁能比农人更懂一棵蒺藜,更懂大地,更懂那些生活的本质呢?俗语说:“要知朝中事,乡间问老农”,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嘛。
“屈人”屈不了白老汉
蒺藜初生刺软,待秋天成熟变黄时,周围的草又为它打了掩护,所以,它像一枚隐身于草丛的暗器,冷不丁就会偷袭。当年的乡民们没少挨过扎,可是,凡事皆有例外,要说我们村的白老汉,就不服蒺藜。
大家都不太晓得白老汉的年龄,总之其晚年大约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家要比一般人家穷困,所以,除了寒冷季节,他是常年不穿鞋的。春天稍一暖和,就开始打赤膊,天冷了,在空膛罩一件旧棉袄,有时连扣子都不系,两个衣襟一抄,就过了冬。
身体吃得消吗?有道是“什么样的衣裳,什么样的毛孔”,这也是我老家的人总结出来的。这句话真算得上真理,它几乎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另一种说法:外界生存环境决定了人(生物)在生理上的适应性变化。
白老汉呢,脚掌磨炼得不怕扎,老茧虽不知有多厚,反正蒺藜是刺不透。一旦试着脚底有蒺藜硌脚,只需把脚板就地一搓,继续大步流星。听人讲,他敢在蒺藜窝里从容行走。
白老汉向来是个爱笑的人,一生不悲观,不忌恨,不说丧气话,一直活到挺大年纪。对于不怕蒺藜,他有这样一句玩笑话被乡邻流传了下来:“布鞋,皮鞋,都不如母亲给的这双‘鞋’啊,皮实,耐穿。”
蒺藜的别名有很多:止行、屈人,可见它的刺有多厉害。不过,它的厉害在白老汉那里行不通,“屈人”屈不了白老汉。
庞涓的骨头变蒺藜
在昌邑北部地带,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庞涓死后,筋变成了“噶拉蔓(葎草)”,骨头变成了蒺藜。
要说庞涓,就不能不提孙膑。战国时期的孙膑与庞涓本为同窗,庞涓在魏国当了大将军之后,请孙膑出山,但庞涓嫉妒孙膑的才能,看不得孙同学比他好,遂设计陷害,结果孙膑受刑身残。之后,孙膑投奔齐国,被齐威王封鄑(今昌邑西北部)为食邑。
至今,昌北仍建有孙子庙,并且每年都要举行“发大牛”的祭祀活动(孙膑腿脚不便,当时巡视乡里,体察民情时,靠骑牛行走)。
当地百姓通过一段史实,认为庞涓心胸狭隘,阴险狡诈,所以就编排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他死后仍品性不改,还要变成葎草和蒺藜来扎得人“哎哟”,似乎他的魂灵存了陷害好人的恶意,却只能投生出“四下里跑”的卑微。那又如何?反正,要被白老汉一脚搓出老远。
有些植物,因其特殊的生理属性和生长习性,注定要与人类产生密切的联系,碰撞出更多的精彩故事。比如,蒺藜。
把它藏进谜语里
植物被编进谜语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棵草,四下里跑,开黄花,结‘哎哟儿’”,这就是我老家的人为蒺藜量身打造的谜语。蒺藜会匍匐攀爬,花为黄色。“跑”,是指它以根基为圆心,努力扩大半径往外生长的蓬勃状态。“哎哟”,本是人被蒺藜刺扎时的一个本能反应,并非对植物特性的直接描述,但乡里人的语言总是那么切中要点,直接把这声惊叫具化为一个果实的样子。
还有谁能比农人更懂一棵蒺藜,更懂大地,更懂那些生活的本质呢?俗语说:“要知朝中事,乡间问老农”,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嘛。
“屈人”屈不了白老汉
蒺藜初生刺软,待秋天成熟变黄时,周围的草又为它打了掩护,所以,它像一枚隐身于草丛的暗器,冷不丁就会偷袭。当年的乡民们没少挨过扎,可是,凡事皆有例外,要说我们村的白老汉,就不服蒺藜。
大家都不太晓得白老汉的年龄,总之其晚年大约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家要比一般人家穷困,所以,除了寒冷季节,他是常年不穿鞋的。春天稍一暖和,就开始打赤膊,天冷了,在空膛罩一件旧棉袄,有时连扣子都不系,两个衣襟一抄,就过了冬。
身体吃得消吗?有道是“什么样的衣裳,什么样的毛孔”,这也是我老家的人总结出来的。这句话真算得上真理,它几乎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另一种说法:外界生存环境决定了人(生物)在生理上的适应性变化。
白老汉呢,脚掌磨炼得不怕扎,老茧虽不知有多厚,反正蒺藜是刺不透。一旦试着脚底有蒺藜硌脚,只需把脚板就地一搓,继续大步流星。听人讲,他敢在蒺藜窝里从容行走。
白老汉向来是个爱笑的人,一生不悲观,不忌恨,不说丧气话,一直活到挺大年纪。对于不怕蒺藜,他有这样一句玩笑话被乡邻流传了下来:“布鞋,皮鞋,都不如母亲给的这双‘鞋’啊,皮实,耐穿。”
蒺藜的别名有很多:止行、屈人,可见它的刺有多厉害。不过,它的厉害在白老汉那里行不通,“屈人”屈不了白老汉。
庞涓的骨头变蒺藜
在昌邑北部地带,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庞涓死后,筋变成了“噶拉蔓(葎草)”,骨头变成了蒺藜。
要说庞涓,就不能不提孙膑。战国时期的孙膑与庞涓本为同窗,庞涓在魏国当了大将军之后,请孙膑出山,但庞涓嫉妒孙膑的才能,看不得孙同学比他好,遂设计陷害,结果孙膑受刑身残。之后,孙膑投奔齐国,被齐威王封鄑(今昌邑西北部)为食邑。
至今,昌北仍建有孙子庙,并且每年都要举行“发大牛”的祭祀活动(孙膑腿脚不便,当时巡视乡里,体察民情时,靠骑牛行走)。
当地百姓通过一段史实,认为庞涓心胸狭隘,阴险狡诈,所以就编排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他死后仍品性不改,还要变成葎草和蒺藜来扎得人“哎哟”,似乎他的魂灵存了陷害好人的恶意,却只能投生出“四下里跑”的卑微。那又如何?反正,要被白老汉一脚搓出老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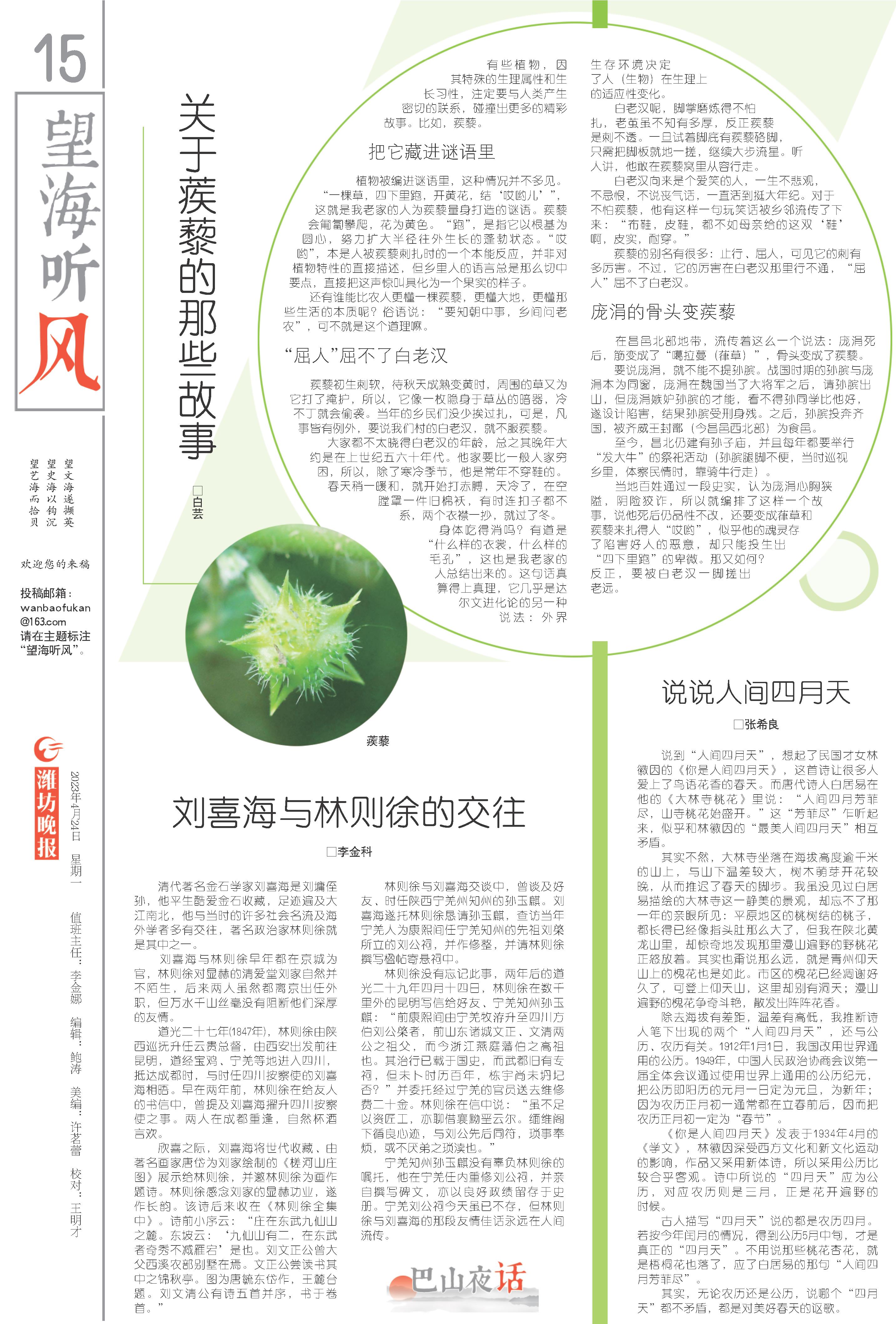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424/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