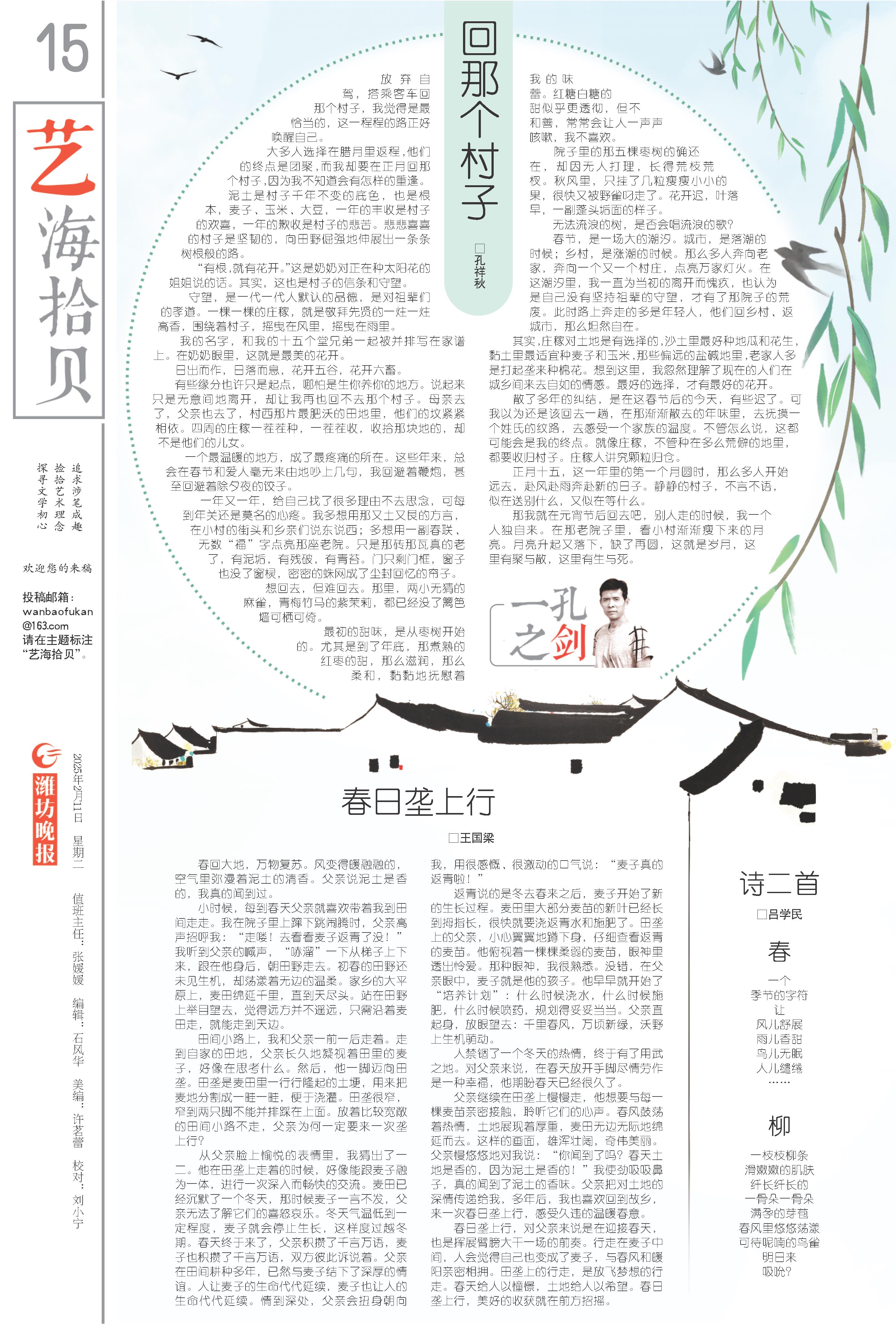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元宵
圆满
□孔祥秋
放弃自驾,搭乘客车回那个村子,我觉得是最恰当的,这一程程的路正好唤醒自己。
大多人选择在腊月里返程,他们的终点是团聚,而我却要在正月回那个村子,因为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重逢。
泥土是村子千年不变的底色,也是根本,麦子、玉米、大豆,一年的丰收是村子的欢喜,一年的歉收是村子的悲苦。悲悲喜喜的村子是坚韧的,向田野倔强地伸展出一条条树根般的路。
“有根,就有花开。”这是奶奶对正在种太阳花的姐姐说的话。其实,这也是村子的信条和守望。
守望,是一代一代人默认的品德,是对祖辈们的孝道。一棵一棵的庄稼,就是敬拜先贤的一炷一炷高香,围绕着村子,摇曳在风里,摇曳在雨里。
我的名字,和我的十五个堂兄弟一起被并排写在家谱上。在奶奶眼里,这就是最美的花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花开五谷,花开六畜。
有些缘分也许只是起点,哪怕是生你养你的地方。说起来只是无意间地离开,却让我再也回不去那个村子。母亲去了,父亲也去了,村西那片最肥沃的田地里,他们的坟紧紧相依。四周的庄稼一茬茬种,一茬茬收,收拾那块地的,却不是他们的儿女。
一个最温暖的地方,成了最疼痛的所在。这些年来,总会在春节和爱人毫无来由地吵上几句,我回避着鞭炮,甚至回避着除夕夜的饺子。
一年又一年,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不去思念,可每到年关还是莫名的心疼。我多想用那又土又艮的方言,在小村的街头和乡亲们说东说西;多想用一副春联、无数“福”字点亮那座老院。只是那砖那瓦真的老了,有泥垢,有残破,有青苔。门只剩门框,窗子也没了窗棂,密密的蛛网成了尘封回忆的帘子。
想回去,但难回去。那里,两小无猜的麻雀,青梅竹马的紫茉莉,都已经没了篱笆墙可栖可倚。
最初的甜味,是从枣树开始的。尤其是到了年底,那煮熟的红枣的甜,那么滋润,那么柔和,黏黏地抚慰着我的味蕾。红糖白糖的甜似乎更透彻,但不和善,常常会让人一声声咳嗽,我不喜欢。
院子里的那五棵枣树的确还在,却因无人打理,长得荒枝荒杈。秋风里,只挂了几粒瘦瘦小小的果,很快又被野雀叼走了。花开迟,叶落早,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
无法流浪的树,是否会唱流浪的歌?
春节,是一场大的潮汐。城市,是落潮的时候;乡村,是涨潮的时候。那么多人奔向老家,奔向一个又一个村庄,点亮万家灯火。在这潮汐里,我一直为当初的离开而愧疚,也认为是自己没有坚持祖辈的守望,才有了那院子的荒废。此时路上奔走的多是年轻人,他们回乡村、返城市,那么坦然自在。
其实,庄稼对土地是有选择的,沙土里最好种地瓜和花生,黏土里最适宜种麦子和玉米,那些偏远的盐碱地里,老家人多是打起垄来种棉花。想到这里,我忽然理解了现在的人们在城乡间来去自如的情感。最好的选择,才有最好的花开。
散了多年的纠结,是在这春节后的今天,有些迟了。可我以为还是该回去一趟,在那渐渐散去的年味里,去抚摸一个姓氏的纹路,去感受一个家族的温度。不管怎么说,这都可能会是我的终点。就像庄稼,不管种在多么荒僻的地里,都要收归村子。庄稼人讲究颗粒归仓。
正月十五,这一年里的第一个月圆时,那么多人开始远去,赴风赴雨奔赴新的日子。静静的村子,不言不语,似在送别什么,又似在等什么。
那我就在元宵节后回去吧,别人走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来。在那老院子里,看小村渐渐瘦下来的月亮。月亮升起又落下,缺了再圆,这就是岁月,这里有聚与散,这里有生与死。
放弃自驾,搭乘客车回那个村子,我觉得是最恰当的,这一程程的路正好唤醒自己。
大多人选择在腊月里返程,他们的终点是团聚,而我却要在正月回那个村子,因为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重逢。
泥土是村子千年不变的底色,也是根本,麦子、玉米、大豆,一年的丰收是村子的欢喜,一年的歉收是村子的悲苦。悲悲喜喜的村子是坚韧的,向田野倔强地伸展出一条条树根般的路。
“有根,就有花开。”这是奶奶对正在种太阳花的姐姐说的话。其实,这也是村子的信条和守望。
守望,是一代一代人默认的品德,是对祖辈们的孝道。一棵一棵的庄稼,就是敬拜先贤的一炷一炷高香,围绕着村子,摇曳在风里,摇曳在雨里。
我的名字,和我的十五个堂兄弟一起被并排写在家谱上。在奶奶眼里,这就是最美的花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花开五谷,花开六畜。
有些缘分也许只是起点,哪怕是生你养你的地方。说起来只是无意间地离开,却让我再也回不去那个村子。母亲去了,父亲也去了,村西那片最肥沃的田地里,他们的坟紧紧相依。四周的庄稼一茬茬种,一茬茬收,收拾那块地的,却不是他们的儿女。
一个最温暖的地方,成了最疼痛的所在。这些年来,总会在春节和爱人毫无来由地吵上几句,我回避着鞭炮,甚至回避着除夕夜的饺子。
一年又一年,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不去思念,可每到年关还是莫名的心疼。我多想用那又土又艮的方言,在小村的街头和乡亲们说东说西;多想用一副春联、无数“福”字点亮那座老院。只是那砖那瓦真的老了,有泥垢,有残破,有青苔。门只剩门框,窗子也没了窗棂,密密的蛛网成了尘封回忆的帘子。
想回去,但难回去。那里,两小无猜的麻雀,青梅竹马的紫茉莉,都已经没了篱笆墙可栖可倚。
最初的甜味,是从枣树开始的。尤其是到了年底,那煮熟的红枣的甜,那么滋润,那么柔和,黏黏地抚慰着我的味蕾。红糖白糖的甜似乎更透彻,但不和善,常常会让人一声声咳嗽,我不喜欢。
院子里的那五棵枣树的确还在,却因无人打理,长得荒枝荒杈。秋风里,只挂了几粒瘦瘦小小的果,很快又被野雀叼走了。花开迟,叶落早,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
无法流浪的树,是否会唱流浪的歌?
春节,是一场大的潮汐。城市,是落潮的时候;乡村,是涨潮的时候。那么多人奔向老家,奔向一个又一个村庄,点亮万家灯火。在这潮汐里,我一直为当初的离开而愧疚,也认为是自己没有坚持祖辈的守望,才有了那院子的荒废。此时路上奔走的多是年轻人,他们回乡村、返城市,那么坦然自在。
其实,庄稼对土地是有选择的,沙土里最好种地瓜和花生,黏土里最适宜种麦子和玉米,那些偏远的盐碱地里,老家人多是打起垄来种棉花。想到这里,我忽然理解了现在的人们在城乡间来去自如的情感。最好的选择,才有最好的花开。
散了多年的纠结,是在这春节后的今天,有些迟了。可我以为还是该回去一趟,在那渐渐散去的年味里,去抚摸一个姓氏的纹路,去感受一个家族的温度。不管怎么说,这都可能会是我的终点。就像庄稼,不管种在多么荒僻的地里,都要收归村子。庄稼人讲究颗粒归仓。
正月十五,这一年里的第一个月圆时,那么多人开始远去,赴风赴雨奔赴新的日子。静静的村子,不言不语,似在送别什么,又似在等什么。
那我就在元宵节后回去吧,别人走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来。在那老院子里,看小村渐渐瘦下来的月亮。月亮升起又落下,缺了再圆,这就是岁月,这里有聚与散,这里有生与死。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211/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