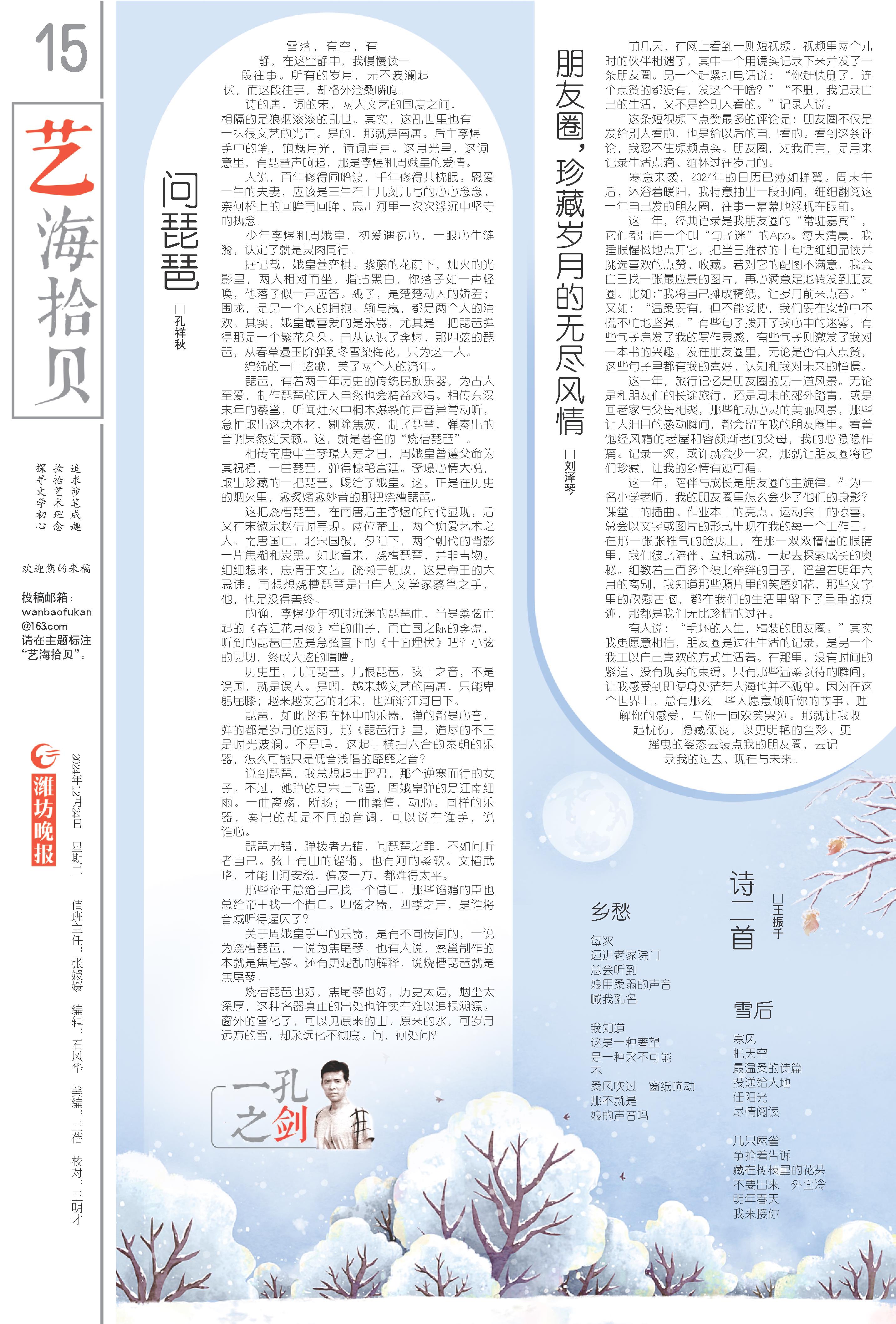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非遗日历
开启新年
 14版:康养周刊
14版:康养周刊
- * 避开脑卒中的十大误区
- * 老年人冬季如何养胃
- *
改善老年人贫血
专家这样建议
 15版:艺海拾贝
15版:艺海拾贝
- * 问琵琶
- * 朋友圈,珍藏岁月的无尽风情
- * 诗二首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神奇的冰花
□孔祥秋
雪落,有空,有静,在这空静中,我慢慢读一段往事。所有的岁月,无不波澜起伏,而这段往事,却格外沧桑嶙峋。
诗的唐,词的宋,两大文艺的国度之间,相隔的是狼烟滚滚的乱世。其实,这乱世里也有一抹很文艺的光芒。是的,那就是南唐。后主李煜手中的笔,饱蘸月光,诗词声声。这月光里,这词意里,有琵琶声响起,那是李煜和周娥皇的爱情。
人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恩爱一生的夫妻,应该是三生石上几刻几写的心心念念、奈何桥上的回眸再回眸、忘川河里一次次浮沉中坚守的执念。
少年李煜和周娥皇,初爱遇初心,一眼心生涟漪,认定了就是灵肉同行。
据记载,娥皇善弈棋。紫藤的花荫下,烛火的光影里,两人相对而坐,指拈黑白,你落子如一声轻唤,他落子似一声应答。孤子,是楚楚动人的娇羞;围龙,是另一个人的拥抱。输与赢,都是两个人的清欢。其实,娥皇最喜爱的是乐器,尤其是一把琵琶弹得那是一个繁花朵朵。自从认识了李煜,那四弦的琵琶,从春草漫玉阶弹到冬雪染梅花,只为这一人。
绵绵的一曲弦歌,美了两个人的流年。
琵琶,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传统民族乐器,为古人至爱,制作琵琶的匠人自然也会精益求精。相传东汉末年的蔡邕,听闻灶火中桐木爆裂的声音异常动听,急忙取出这块木材,剔除焦灰,制了琵琶,弹奏出的音调果然如天籁。这,就是著名的“烧槽琵琶”。
相传南唐中主李璟大寿之日,周娥皇曾遵父命为其祝福,一曲琵琶,弹得惊艳宫廷。李璟心情大悦,取出珍藏的一把琵琶,赐给了娥皇。这,正是在历史的烟火里,愈炙烤愈妙音的那把烧槽琵琶。
这把烧槽琵琶,在南唐后主李煜的时代显现,后又在宋徽宗赵佶时再现。两位帝王,两个痴爱艺术之人。南唐国亡,北宋国破,夕阳下,两个朝代的背影一片焦糊和炭黑。如此看来,烧槽琵琶,并非吉物。细细想来,忘情于文艺,疏懒于朝政,这是帝王的大忌讳。再想想烧槽琵琶是出自大文学家蔡邕之手,他,也是没得善终。
的确,李煜少年初时沉迷的琵琶曲,当是柔弦而起的《春江花月夜》样的曲子,而亡国之际的李煜,听到的琵琶曲应是急弦直下的《十面埋伏》吧?小弦的切切,终成大弦的嘈嘈。
历史里,几问琵琶,几恨琵琶,弦上之音,不是误国,就是误人。是啊,越来越文艺的南唐,只能卑躬屈膝;越来越文艺的北宋,也渐渐江河日下。
琵琶,如此竖抱在怀中的乐器,弹的都是心音,弹的都是岁月的烟雨,那《琵琶行》里,道尽的不正是时光波澜。不是吗,这起于横扫六合的秦朝的乐器,怎么可能只是低音浅唱的靡靡之音?
说到琵琶,我总想起王昭君,那个逆寒而行的女子。不过,她弹的是塞上飞雪,周娥皇弹的是江南细雨。一曲离殇,断肠;一曲柔情,动心。同样的乐器,奏出的却是不同的音调,可以说在谁手,说谁心。
琵琶无错,弹拨者无错,问琵琶之罪,不如问听者自己。弦上有山的铿锵,也有河的柔软。文韬武略,才能山河安稳,偏废一方,都难得太平。
那些帝王总给自己找一个借口,那些谄媚的臣也总给帝王找一个借口。四弦之器,四季之声,是谁将音域听得逼仄了?
关于周娥皇手中的乐器,是有不同传闻的,一说为烧槽琵琶,一说为焦尾琴。也有人说,蔡邕制作的本就是焦尾琴。还有更混乱的解释,说烧槽琵琶就是焦尾琴。
烧槽琵琶也好,焦尾琴也好,历史太远,烟尘太深厚,这种名器真正的出处也许实在难以追根溯源。窗外的雪化了,可以见原来的山、原来的水,可岁月远方的雪,却永远化不彻底。问,何处问?
雪落,有空,有静,在这空静中,我慢慢读一段往事。所有的岁月,无不波澜起伏,而这段往事,却格外沧桑嶙峋。
诗的唐,词的宋,两大文艺的国度之间,相隔的是狼烟滚滚的乱世。其实,这乱世里也有一抹很文艺的光芒。是的,那就是南唐。后主李煜手中的笔,饱蘸月光,诗词声声。这月光里,这词意里,有琵琶声响起,那是李煜和周娥皇的爱情。
人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恩爱一生的夫妻,应该是三生石上几刻几写的心心念念、奈何桥上的回眸再回眸、忘川河里一次次浮沉中坚守的执念。
少年李煜和周娥皇,初爱遇初心,一眼心生涟漪,认定了就是灵肉同行。
据记载,娥皇善弈棋。紫藤的花荫下,烛火的光影里,两人相对而坐,指拈黑白,你落子如一声轻唤,他落子似一声应答。孤子,是楚楚动人的娇羞;围龙,是另一个人的拥抱。输与赢,都是两个人的清欢。其实,娥皇最喜爱的是乐器,尤其是一把琵琶弹得那是一个繁花朵朵。自从认识了李煜,那四弦的琵琶,从春草漫玉阶弹到冬雪染梅花,只为这一人。
绵绵的一曲弦歌,美了两个人的流年。
琵琶,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传统民族乐器,为古人至爱,制作琵琶的匠人自然也会精益求精。相传东汉末年的蔡邕,听闻灶火中桐木爆裂的声音异常动听,急忙取出这块木材,剔除焦灰,制了琵琶,弹奏出的音调果然如天籁。这,就是著名的“烧槽琵琶”。
相传南唐中主李璟大寿之日,周娥皇曾遵父命为其祝福,一曲琵琶,弹得惊艳宫廷。李璟心情大悦,取出珍藏的一把琵琶,赐给了娥皇。这,正是在历史的烟火里,愈炙烤愈妙音的那把烧槽琵琶。
这把烧槽琵琶,在南唐后主李煜的时代显现,后又在宋徽宗赵佶时再现。两位帝王,两个痴爱艺术之人。南唐国亡,北宋国破,夕阳下,两个朝代的背影一片焦糊和炭黑。如此看来,烧槽琵琶,并非吉物。细细想来,忘情于文艺,疏懒于朝政,这是帝王的大忌讳。再想想烧槽琵琶是出自大文学家蔡邕之手,他,也是没得善终。
的确,李煜少年初时沉迷的琵琶曲,当是柔弦而起的《春江花月夜》样的曲子,而亡国之际的李煜,听到的琵琶曲应是急弦直下的《十面埋伏》吧?小弦的切切,终成大弦的嘈嘈。
历史里,几问琵琶,几恨琵琶,弦上之音,不是误国,就是误人。是啊,越来越文艺的南唐,只能卑躬屈膝;越来越文艺的北宋,也渐渐江河日下。
琵琶,如此竖抱在怀中的乐器,弹的都是心音,弹的都是岁月的烟雨,那《琵琶行》里,道尽的不正是时光波澜。不是吗,这起于横扫六合的秦朝的乐器,怎么可能只是低音浅唱的靡靡之音?
说到琵琶,我总想起王昭君,那个逆寒而行的女子。不过,她弹的是塞上飞雪,周娥皇弹的是江南细雨。一曲离殇,断肠;一曲柔情,动心。同样的乐器,奏出的却是不同的音调,可以说在谁手,说谁心。
琵琶无错,弹拨者无错,问琵琶之罪,不如问听者自己。弦上有山的铿锵,也有河的柔软。文韬武略,才能山河安稳,偏废一方,都难得太平。
那些帝王总给自己找一个借口,那些谄媚的臣也总给帝王找一个借口。四弦之器,四季之声,是谁将音域听得逼仄了?
关于周娥皇手中的乐器,是有不同传闻的,一说为烧槽琵琶,一说为焦尾琴。也有人说,蔡邕制作的本就是焦尾琴。还有更混乱的解释,说烧槽琵琶就是焦尾琴。
烧槽琵琶也好,焦尾琴也好,历史太远,烟尘太深厚,这种名器真正的出处也许实在难以追根溯源。窗外的雪化了,可以见原来的山、原来的水,可岁月远方的雪,却永远化不彻底。问,何处问?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24/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