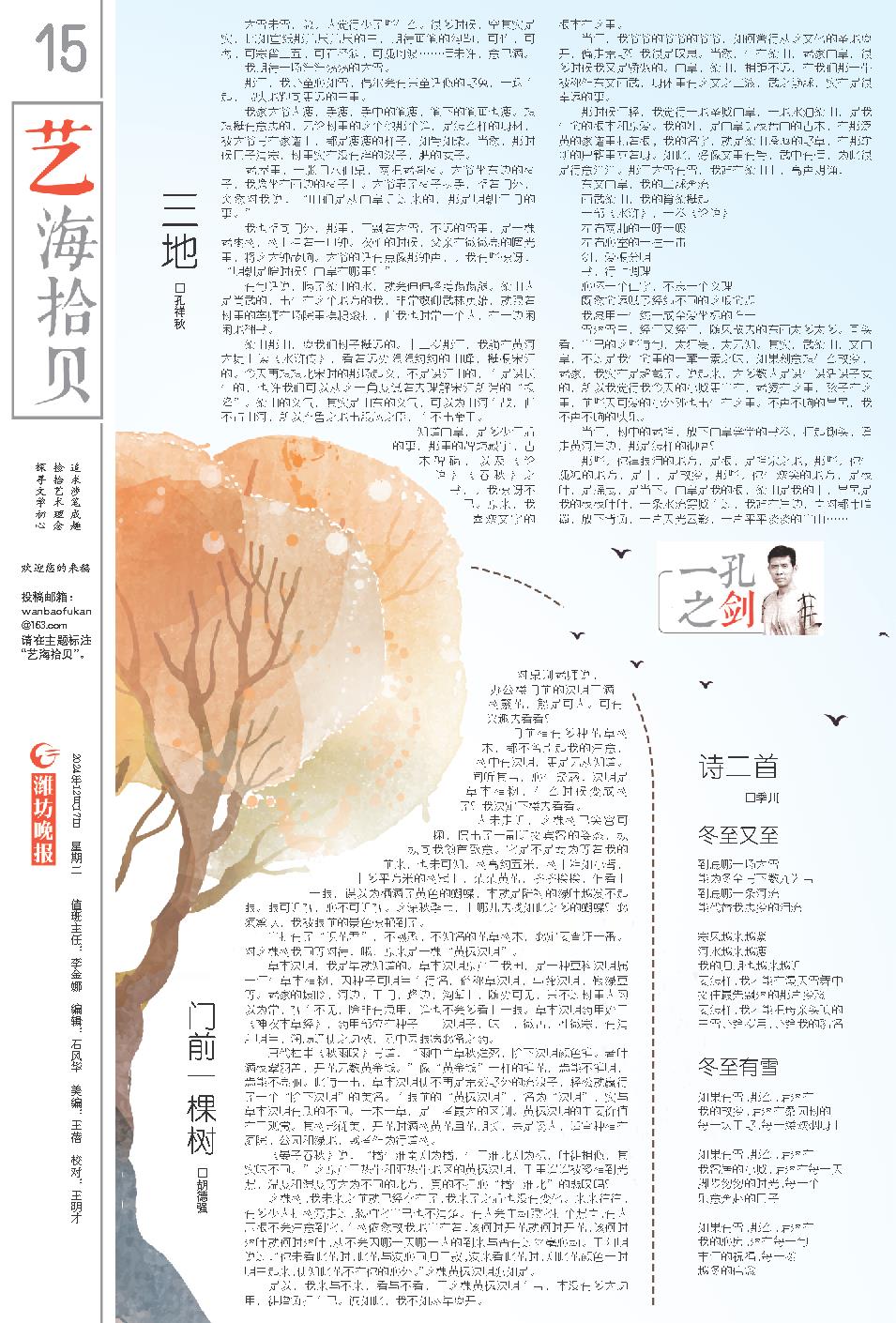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蛇年年画
赶印上架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等一场雪落
□孔祥秋
大雪未雪,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很多时候,空其实是实,比如宣纸那几尺几尺的白,期待画笔的勾勒,可竹、可梅、可寒雀三五、可石径斜、可孤舟渡……情未许,意已满。
我期待一场浩浩荡荡的大雪。
那年,我还童心如雪,偶尔会有只童话似的野兔,一跃而起,飞快地跑向更远的白里。
我家大爷人瘦,手瘦,手中的笔瘦,笔下的笔画也瘦。想想挺有意思的,无论村里的这个他那个谁,是怎么样的身材,被大爷写在家谱上,都是瘦瘦的样子,如骨如柴。当然,那时候日子清寒,村里实在没有胖的汉子、肥的女子。
老屋里,一张旧八仙桌,两把老圈椅。大爷坐东边的椅子,我跪坐在西边的椅子上。大爷靠了椅子扶手,望着门外,突然对我说:“咱们是从曲阜迁过来的,那是明朝年间的事。”
我也望向门外,那里,正飘着大雪,不远的雪里,是一棵老枣树,树上挂着一口钟。农忙的时候,父亲在微微亮的曙光里,将这大钟敲响。大爷的话有点像那钟声,让我有些惊讶:“明朝是啥时候?曲阜在哪里?”
有句话说,喝了梁山的水,就会伸伸胳膊踢踢腿。梁山人是尚武的,出生在这个地方的我,非常敬仰武林英雄,就跟着村里的拳师在场院里摸爬滚打,但我也时常一个人,在一边闲闲地翻书。
梁山那山,离我们村子挺远的。十三岁那年,我躺在黄河大堤上读《水浒传》,看着远处隐隐约约的山峰,挺恨宋江的。今天再想想北宋时的那场起义,不是谋江山的,而是谋民生的,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试着去理解宋江所谓的“投降”。梁山的义气,其实是山东的义气,可以为山河而战,但不占山河,所以齐鲁之地出股肱之臣,而不出帝王。
知道曲阜,是多少年后的事,那里的牌坊殿宇、古木碑碣,以及《论语》《春秋》之书,让我惊讶不已。原来,我喜欢文字的根本在这里。
当年,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如何舍得从这文化的圣地离开,偏走荒野?我很是叹息。当然,生在梁山,老家曲阜,很多时候我又是骄傲的。曲阜、梁山,相距不远,在我们那一带被称作东文西武,身体里有这文之血液,武之筋脉,实在是很幸运的事。
那时候年轻,我觉得一地圣城曲阜,一地水泊梁山,是我生命的根本和原爱。我的姓,是曲阜虬枝盘曲的古木,在那泛黄的家谱里扎着根;我的名字,就是梁山逶迤的野草,在那崭新的户籍里立着身。如此,好像文里有骨,武中有情,为此很是得意洋洋。那年大雪有雪,我站在梁山上,高声朗诵:
东文曲阜,我的血脉奔流
西武梁山,我的脊梁挺起
一部《水浒》,一卷《论语》
左右两肺的一呼一吸
左右心室的一撞一击
剑,爱恨分明
书,行止调理
心怀一个仁字,不忘一个义理
既然命运赋予经纬不同的这般命题
我愿用一生统一成至爱坐标的唯一
雪落雪白,经年又经年,随风散去的东西太多太多。回头看,自己的这些诗句,太狂妄、太无知。其实,武梁山,文曲阜,不过是我生命里的一荤一素之味,如果刻意想什么故乡、老家,我实在是超载了。说起来,大多数人是谋生谋活谋子女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的小城更自在,老婆在这里,孩子在这里,前些天可爱的小外孙也出生在这里。不声不响的昌邑,我不声不响的快乐。
当年,村中的老祖,放下曲阜学堂的书卷,扛起锄头,遥走黄河岸边,那是怎样的彻悟?
那些让你掉眼泪的地方,是根,是祖宗之地;那些让你生孤独的地方,是干,是故乡;那些让你生欢笑的地方,是枝叶,是摇曳,是当下。曲阜是我的根,梁山是我的干,昌邑是我的枝枝叶叶,一条水流穿城而过,我站在岸边,面对都市喧嚣,放下背负,一片天光云影,一片平平淡淡的自由……
大雪未雪,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很多时候,空其实是实,比如宣纸那几尺几尺的白,期待画笔的勾勒,可竹、可梅、可寒雀三五、可石径斜、可孤舟渡……情未许,意已满。
我期待一场浩浩荡荡的大雪。
那年,我还童心如雪,偶尔会有只童话似的野兔,一跃而起,飞快地跑向更远的白里。
我家大爷人瘦,手瘦,手中的笔瘦,笔下的笔画也瘦。想想挺有意思的,无论村里的这个他那个谁,是怎么样的身材,被大爷写在家谱上,都是瘦瘦的样子,如骨如柴。当然,那时候日子清寒,村里实在没有胖的汉子、肥的女子。
老屋里,一张旧八仙桌,两把老圈椅。大爷坐东边的椅子,我跪坐在西边的椅子上。大爷靠了椅子扶手,望着门外,突然对我说:“咱们是从曲阜迁过来的,那是明朝年间的事。”
我也望向门外,那里,正飘着大雪,不远的雪里,是一棵老枣树,树上挂着一口钟。农忙的时候,父亲在微微亮的曙光里,将这大钟敲响。大爷的话有点像那钟声,让我有些惊讶:“明朝是啥时候?曲阜在哪里?”
有句话说,喝了梁山的水,就会伸伸胳膊踢踢腿。梁山人是尚武的,出生在这个地方的我,非常敬仰武林英雄,就跟着村里的拳师在场院里摸爬滚打,但我也时常一个人,在一边闲闲地翻书。
梁山那山,离我们村子挺远的。十三岁那年,我躺在黄河大堤上读《水浒传》,看着远处隐隐约约的山峰,挺恨宋江的。今天再想想北宋时的那场起义,不是谋江山的,而是谋民生的,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试着去理解宋江所谓的“投降”。梁山的义气,其实是山东的义气,可以为山河而战,但不占山河,所以齐鲁之地出股肱之臣,而不出帝王。
知道曲阜,是多少年后的事,那里的牌坊殿宇、古木碑碣,以及《论语》《春秋》之书,让我惊讶不已。原来,我喜欢文字的根本在这里。
当年,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如何舍得从这文化的圣地离开,偏走荒野?我很是叹息。当然,生在梁山,老家曲阜,很多时候我又是骄傲的。曲阜、梁山,相距不远,在我们那一带被称作东文西武,身体里有这文之血液,武之筋脉,实在是很幸运的事。
那时候年轻,我觉得一地圣城曲阜,一地水泊梁山,是我生命的根本和原爱。我的姓,是曲阜虬枝盘曲的古木,在那泛黄的家谱里扎着根;我的名字,就是梁山逶迤的野草,在那崭新的户籍里立着身。如此,好像文里有骨,武中有情,为此很是得意洋洋。那年大雪有雪,我站在梁山上,高声朗诵:
东文曲阜,我的血脉奔流
西武梁山,我的脊梁挺起
一部《水浒》,一卷《论语》
左右两肺的一呼一吸
左右心室的一撞一击
剑,爱恨分明
书,行止调理
心怀一个仁字,不忘一个义理
既然命运赋予经纬不同的这般命题
我愿用一生统一成至爱坐标的唯一
雪落雪白,经年又经年,随风散去的东西太多太多。回头看,自己的这些诗句,太狂妄、太无知。其实,武梁山,文曲阜,不过是我生命里的一荤一素之味,如果刻意想什么故乡、老家,我实在是超载了。说起来,大多数人是谋生谋活谋子女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的小城更自在,老婆在这里,孩子在这里,前些天可爱的小外孙也出生在这里。不声不响的昌邑,我不声不响的快乐。
当年,村中的老祖,放下曲阜学堂的书卷,扛起锄头,遥走黄河岸边,那是怎样的彻悟?
那些让你掉眼泪的地方,是根,是祖宗之地;那些让你生孤独的地方,是干,是故乡;那些让你生欢笑的地方,是枝叶,是摇曳,是当下。曲阜是我的根,梁山是我的干,昌邑是我的枝枝叶叶,一条水流穿城而过,我站在岸边,面对都市喧嚣,放下背负,一片天光云影,一片平平淡淡的自由……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217/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