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奇幻之夜
□肖刚
上世纪70年代,父亲工作调动,离家的路从五里一下子延长到五十里。手里攥着调令,父亲不知该如何向母亲开口。那时,奶奶正瘫痪在床,我们姐弟三个,大的九岁,小的才三岁。
到县城上班后的第一个周末,父亲心急火燎地往家赶,以为家里肯定乱成一锅粥。没想到回到家,一切井然有序,院子里整整齐齐,我们穿得干干净净,房间被整理得清清爽爽。奶奶盖的被褥刚晒过,散发着阳光的味道。父亲望着累得黑瘦的母亲,眼圈发红。
母亲小时候聪明好学,成绩优异,上完初中后,为了让大舅有书念,她主动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小小年纪就挣工分贴补家用。父母结婚那天,大舅掏着心窝子对父亲说:“我对不起小妹,如果不是当年家里穷,小妹现在也该是公家人了!”那时,能从山窝窝里进到城里公干,是庄稼人做梦都在想的事。父亲郑重地向大舅保证:婚后一定要好好对待母亲。结果,这些沉重的担子又落到母亲一个人肩上。
母亲没有诉苦,也没有埋怨,只是一再嘱咐父亲:“在县上,要好好干,我们娘几个才有盼头!”
父亲拼命工作,争取上进,他的画原本就不错,那几年更是勤修苦练,居然慢慢地有了名气。终于,父亲符合条件,为母亲办理了“农转非”手续,那时,由母亲照顾了十几年的奶奶已去世,我们也都上了班。
我们都算出息,先后考上了大学。大姐喜欢唱歌,上班没几年就成为市文工团的台柱子;二姐才华横溢又勤奋,四十岁不到,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酷爱书法,一手狂草写得龙飞风舞,也小有名气。别人都说我们是传承了父亲,父亲却说,这都是母亲的功劳。确实,母亲虽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坚忍、要强,我们都像她。
在农村时,母亲终年劳累落下了一身病,每逢阴雨天就很煎熬,但我们很少听到母亲呻吟。我们知道母亲云淡风轻的背后是咬牙坚持,生活的苦累和老小的依赖把她锤炼成一个坚强的女人。到城里后,母亲也闲不住,先是到棉麻厂做临时工,后来我们姐弟先后有了孩子,又帮着我们看孩子。我们都特别放心把孩子交给母亲。
后来,我们一家应邀去赴宴,司仪一一介绍我们:“这位是著名画家李五一先生,这位是著名歌唱家李梅女士……”介绍到母亲时,面对一个只会做饭带孩子的老太太,司仪忽然哑口无言。我们看到母亲的脸一下子红了,明亮的白炽灯下,她像一个怯场的孩子,又失落又无助。好在那位司仪很快镇静下来,微微一笑,继而大声道:“这位是著名的内当家,最优秀的贤内助——李老的爱人黄姑女士。”一时间,全场掌声雷动。父亲突然直起身来,冲着母亲鞠了一躬,父亲抬起头,我们看到他的眼睛里噙满泪水……
上世纪70年代,父亲工作调动,离家的路从五里一下子延长到五十里。手里攥着调令,父亲不知该如何向母亲开口。那时,奶奶正瘫痪在床,我们姐弟三个,大的九岁,小的才三岁。
到县城上班后的第一个周末,父亲心急火燎地往家赶,以为家里肯定乱成一锅粥。没想到回到家,一切井然有序,院子里整整齐齐,我们穿得干干净净,房间被整理得清清爽爽。奶奶盖的被褥刚晒过,散发着阳光的味道。父亲望着累得黑瘦的母亲,眼圈发红。
母亲小时候聪明好学,成绩优异,上完初中后,为了让大舅有书念,她主动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小小年纪就挣工分贴补家用。父母结婚那天,大舅掏着心窝子对父亲说:“我对不起小妹,如果不是当年家里穷,小妹现在也该是公家人了!”那时,能从山窝窝里进到城里公干,是庄稼人做梦都在想的事。父亲郑重地向大舅保证:婚后一定要好好对待母亲。结果,这些沉重的担子又落到母亲一个人肩上。
母亲没有诉苦,也没有埋怨,只是一再嘱咐父亲:“在县上,要好好干,我们娘几个才有盼头!”
父亲拼命工作,争取上进,他的画原本就不错,那几年更是勤修苦练,居然慢慢地有了名气。终于,父亲符合条件,为母亲办理了“农转非”手续,那时,由母亲照顾了十几年的奶奶已去世,我们也都上了班。
我们都算出息,先后考上了大学。大姐喜欢唱歌,上班没几年就成为市文工团的台柱子;二姐才华横溢又勤奋,四十岁不到,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酷爱书法,一手狂草写得龙飞风舞,也小有名气。别人都说我们是传承了父亲,父亲却说,这都是母亲的功劳。确实,母亲虽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坚忍、要强,我们都像她。
在农村时,母亲终年劳累落下了一身病,每逢阴雨天就很煎熬,但我们很少听到母亲呻吟。我们知道母亲云淡风轻的背后是咬牙坚持,生活的苦累和老小的依赖把她锤炼成一个坚强的女人。到城里后,母亲也闲不住,先是到棉麻厂做临时工,后来我们姐弟先后有了孩子,又帮着我们看孩子。我们都特别放心把孩子交给母亲。
后来,我们一家应邀去赴宴,司仪一一介绍我们:“这位是著名画家李五一先生,这位是著名歌唱家李梅女士……”介绍到母亲时,面对一个只会做饭带孩子的老太太,司仪忽然哑口无言。我们看到母亲的脸一下子红了,明亮的白炽灯下,她像一个怯场的孩子,又失落又无助。好在那位司仪很快镇静下来,微微一笑,继而大声道:“这位是著名的内当家,最优秀的贤内助——李老的爱人黄姑女士。”一时间,全场掌声雷动。父亲突然直起身来,冲着母亲鞠了一躬,父亲抬起头,我们看到他的眼睛里噙满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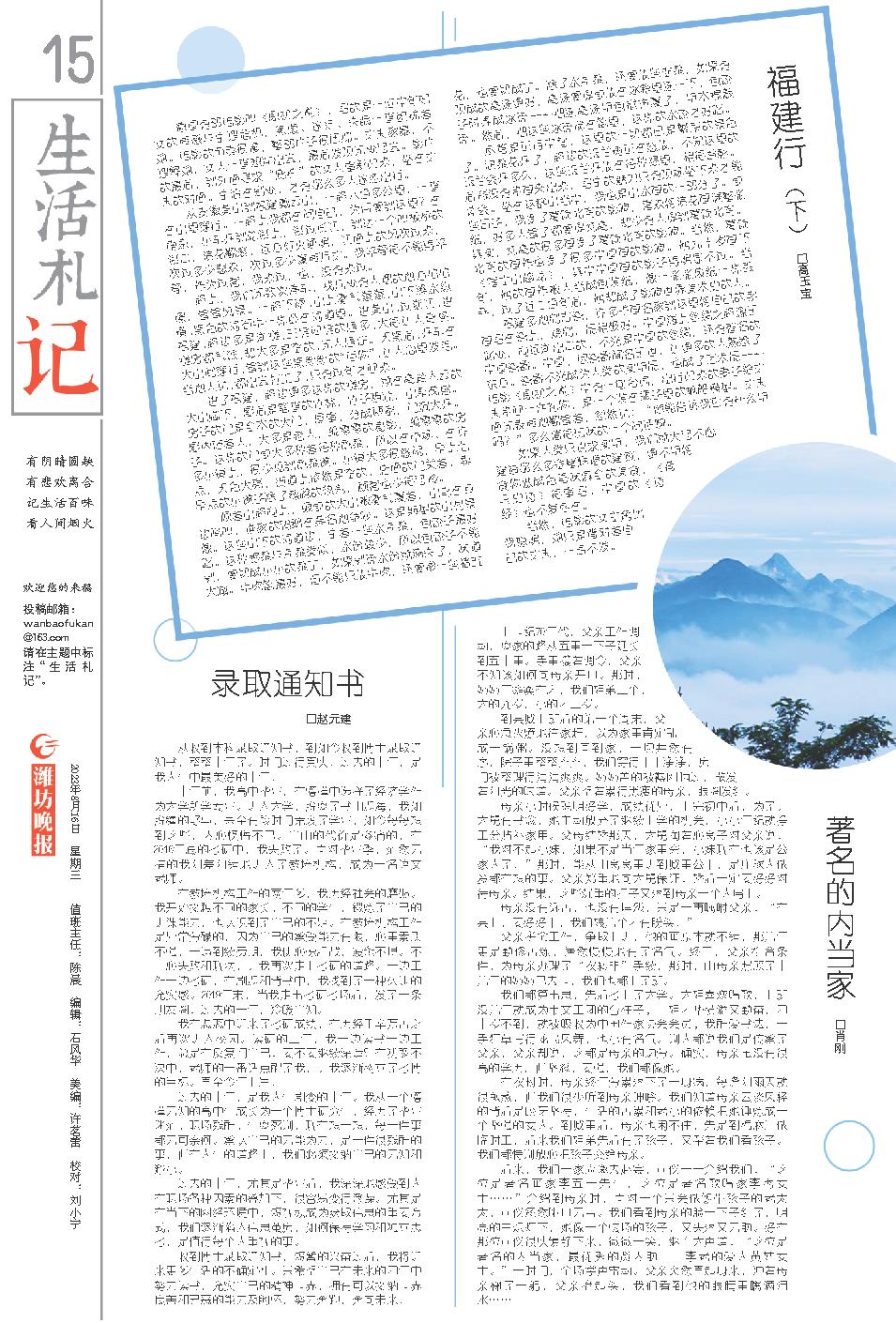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16/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