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停车棚
能发电
 04版:年味
04版:年味
- * 四青年回报桑梓 为村里老人发年货
- * 社区“迎新春 送福字”
- * 迎新春“送万福 进万家”
- * “五老”写福字送居民
- * 生肖兔非遗作品展上线
- * 芝尔庄大集热闹非凡
- * 市人民公园梳妆打扮
 10版:公益广告
10版:公益广告
- * 公益广告
 11版:文娱圈
11版:文娱圈
- * “熟悉的上美回来了”
- * 网友说
 12版:运动吧
12版:运动吧
- * 再见了 那个绿茵场上奔跑的大圣
- * 网友说
- * 洛里宣布从法国国家队退役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腊月de月亮
□马玉顺
又到春节,上世纪70年代过年走亲戚的场景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个年代,在鲁中山区的小山村,大多数家庭还很穷困,一年到头很少吃到小麦粉做的白面饽饽。但是无论自己家里如何,过年走亲戚总不能太寒碜,得装上一些白面饽饽作为礼物。
印象中,小脚的母亲起早贪黑蒸出白面饽饽,装入一个陶瓷瓮中,放在未生火的偏房里,冻得硬梆梆的,放一两个月都不会坏。走亲戚前,母亲掀开瓷瓮的盖板,点着个数将饽饽放进椭圆形箢子里,父亲则把挂在梁头上的一份猪肉取下,放在饽饽上面,用花色的包袱蒙在箢子上。
印象最深的是去舅家、姑家。舅家和姑家在同一个村——赵家峪,离我家20多里路,一半是较为平坦的土路,一半是崎岖的山路,还要穿过一条崮沟、翻越一座山,每一次去都会累得气喘吁吁,汗水直流。但我们毫无怨言,舅舅、姑姑淳朴实在,好吃的好玩的都尽着小辈,每次都是尽兴而归。
小时候,冬天总会飘几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凛冽的北风呼啸而来,吹得人左摇右晃,耳朵鼻头冻得红彤彤。脚踏积雪,走亲戚便添了艰难。有一年,正月初一天降大雪,千里冰封。直到正月初六,我们才决定去舅家和姑家。崮沟覆盖着二三十厘米的冰雪,刚走一段路,棉鞋已冻得硬挺,脚趾麻酥酥地疼,步履变得沉重起来。尽管小心翼翼,但挎箢子的哥哥还是滑倒在山崖雪地上,饽饽滚落出来。赶紧踏着冰雪一步一滑地寻饽饽,累得张口喘气,也没有找全。那天,到达赵家峪时早已过了午饭时间。舅舅和姑姑见到我们大吃一惊,端来红糖水,看着我们喝下后,又强令脱下灌满雪的棉鞋,烤在柴火炉子旁,然后炒菜做饭,招待我们吃饱喝足。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这次历险被反复提及,成为过年走亲戚的一次壮举。
那时,农村鲜有自行车,走亲戚都是步行,走一家亲戚要用一天。午饭一定要在亲戚家吃,虽无大鱼大肉,但粉条白菜、萝卜豆腐,还是够吃的。酒水不名贵,多是地瓜干酿的。通常用锡壶把酒烫得热热的,斟到小酒盅里,宾主边浅酌慢饮,边絮叨着家长里短,那情深深、意长长的温馨,氤氲在几个小时相互谦让的吃喝中。日头西斜,该回家了,亲戚会送出很远很远。
如今,走亲戚也是快节奏,开着汽车一上午就能走好几家。那种慢生活时代走亲戚的隆重仪式感,真是让人怀念啊。
又到春节,上世纪70年代过年走亲戚的场景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个年代,在鲁中山区的小山村,大多数家庭还很穷困,一年到头很少吃到小麦粉做的白面饽饽。但是无论自己家里如何,过年走亲戚总不能太寒碜,得装上一些白面饽饽作为礼物。
印象中,小脚的母亲起早贪黑蒸出白面饽饽,装入一个陶瓷瓮中,放在未生火的偏房里,冻得硬梆梆的,放一两个月都不会坏。走亲戚前,母亲掀开瓷瓮的盖板,点着个数将饽饽放进椭圆形箢子里,父亲则把挂在梁头上的一份猪肉取下,放在饽饽上面,用花色的包袱蒙在箢子上。
印象最深的是去舅家、姑家。舅家和姑家在同一个村——赵家峪,离我家20多里路,一半是较为平坦的土路,一半是崎岖的山路,还要穿过一条崮沟、翻越一座山,每一次去都会累得气喘吁吁,汗水直流。但我们毫无怨言,舅舅、姑姑淳朴实在,好吃的好玩的都尽着小辈,每次都是尽兴而归。
小时候,冬天总会飘几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凛冽的北风呼啸而来,吹得人左摇右晃,耳朵鼻头冻得红彤彤。脚踏积雪,走亲戚便添了艰难。有一年,正月初一天降大雪,千里冰封。直到正月初六,我们才决定去舅家和姑家。崮沟覆盖着二三十厘米的冰雪,刚走一段路,棉鞋已冻得硬挺,脚趾麻酥酥地疼,步履变得沉重起来。尽管小心翼翼,但挎箢子的哥哥还是滑倒在山崖雪地上,饽饽滚落出来。赶紧踏着冰雪一步一滑地寻饽饽,累得张口喘气,也没有找全。那天,到达赵家峪时早已过了午饭时间。舅舅和姑姑见到我们大吃一惊,端来红糖水,看着我们喝下后,又强令脱下灌满雪的棉鞋,烤在柴火炉子旁,然后炒菜做饭,招待我们吃饱喝足。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这次历险被反复提及,成为过年走亲戚的一次壮举。
那时,农村鲜有自行车,走亲戚都是步行,走一家亲戚要用一天。午饭一定要在亲戚家吃,虽无大鱼大肉,但粉条白菜、萝卜豆腐,还是够吃的。酒水不名贵,多是地瓜干酿的。通常用锡壶把酒烫得热热的,斟到小酒盅里,宾主边浅酌慢饮,边絮叨着家长里短,那情深深、意长长的温馨,氤氲在几个小时相互谦让的吃喝中。日头西斜,该回家了,亲戚会送出很远很远。
如今,走亲戚也是快节奏,开着汽车一上午就能走好几家。那种慢生活时代走亲戚的隆重仪式感,真是让人怀念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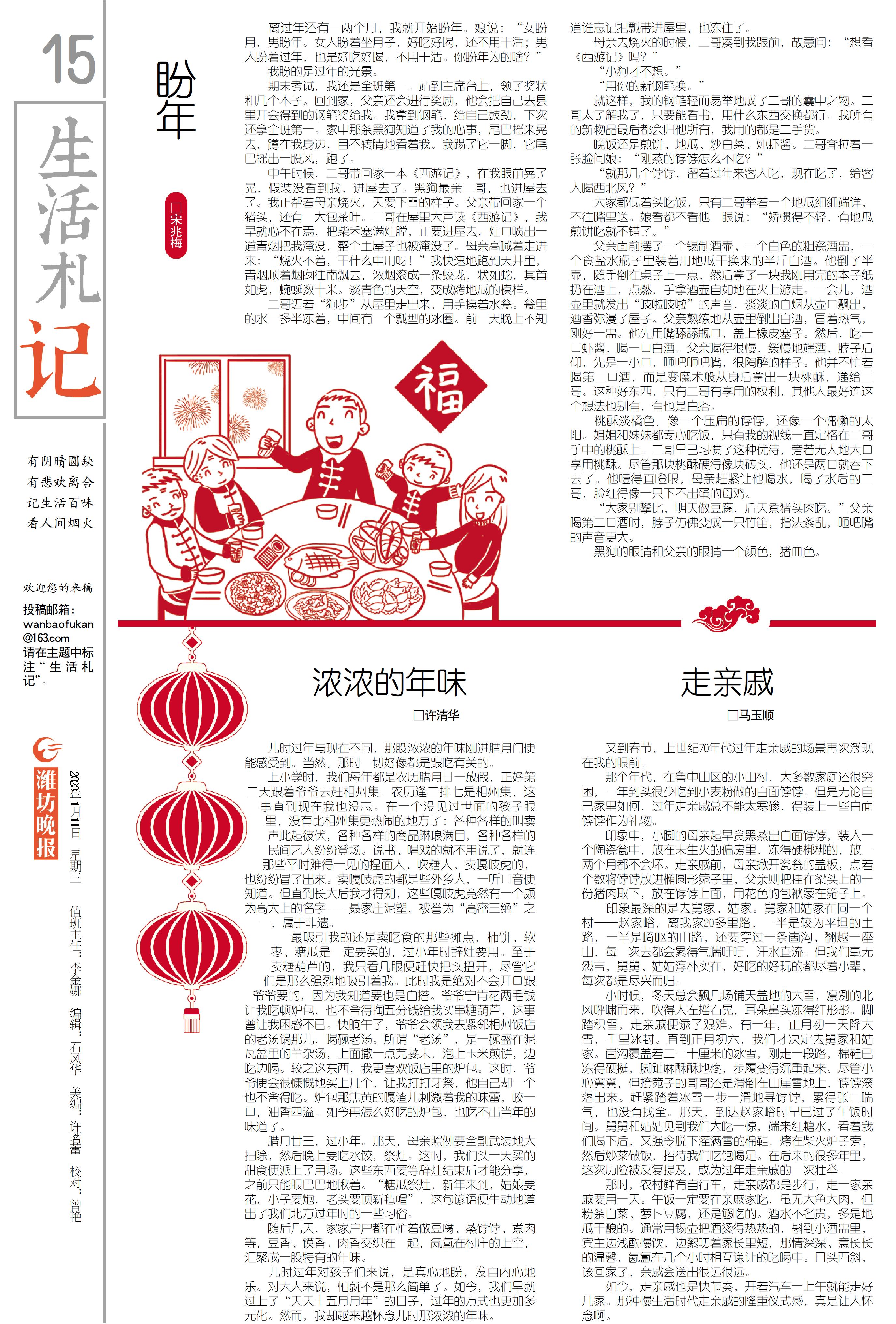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8 09/08 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