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停车棚
能发电
 04版:年味
04版:年味
- * 四青年回报桑梓 为村里老人发年货
- * 社区“迎新春 送福字”
- * 迎新春“送万福 进万家”
- * “五老”写福字送居民
- * 生肖兔非遗作品展上线
- * 芝尔庄大集热闹非凡
- * 市人民公园梳妆打扮
 10版:公益广告
10版:公益广告
- * 公益广告
 11版:文娱圈
11版:文娱圈
- * “熟悉的上美回来了”
- * 网友说
 12版:运动吧
12版:运动吧
- * 再见了 那个绿茵场上奔跑的大圣
- * 网友说
- * 洛里宣布从法国国家队退役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腊月de月亮
□许清华
儿时过年与现在不同,那股浓浓的年味刚进腊月门便能感受到。当然,那时一切好像都是跟吃有关的。
上小学时,我们每年都是农历腊月廿一放假,正好第二天跟着爷爷去赶相州集。农历逢二排七是相州集,这事直到现在我也没忘。在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眼里,没有比相州集更热闹的地方了:各种各样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民间艺人纷纷登场。说书、唱戏的就不用说了,就连那些平时难得一见的捏面人、吹糖人、卖嘎吱虎的,也纷纷冒了出来。卖嘎吱虎的都是些外乡人,一听口音便知道。但直到长大后我才得知,这些嘎吱虎竟然有一个颇为高大上的名字——聂家庄泥塑,被誉为“高密三绝”之一,属于非遗。
最吸引我的还是卖吃食的那些摊点,柿饼、软枣、糖瓜是一定要买的,过小年时辞灶要用。至于卖糖葫芦的,我只看几眼便赶快把头扭开,尽管它们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此时我是绝对不会开口跟爷爷要的,因为我知道要也是白搭。爷爷宁肯花两毛钱让我吃顿炉包,也不舍得掏五分钱给我买串糖葫芦,这事曾让我困惑不已。快晌午了,爷爷会领我去紧邻相州饭店的老汤锅那儿,喝碗老汤。所谓“老汤”,是一碗盛在泥瓦盆里的羊杂汤,上面撒一点芫荽末,泡上玉米煎饼,边吃边喝。较之这东西,我更喜欢饭店里的炉包。这时,爷爷便会很慷慨地买上几个,让我打打牙祭,他自己却一个也不舍得吃。炉包那焦黄的嘎渣儿刺激着我的味蕾,咬一口,油香四溢。如今再怎么好吃的炉包,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腊月廿三,过小年。那天,母亲照例要全副武装地大扫除,然后晚上要吃水饺,祭灶。这时,我们头一天买的甜食便派上了用场。这些东西要等辞灶结束后才能分享,之前只能眼巴巴地瞅着。“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顶新毡帽”,这句谚语便生动地道出了我们北方过年时的一些习俗。
随后几天,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做豆腐、蒸饽饽、煮肉等,豆香、馍香、肉香交织在一起,氤氲在村庄的上空,汇聚成一股特有的年味。
儿时过年对孩子们来说,是真心地盼,发自内心地乐。对大人来说,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如今,我们早就过上了“天天十五月月年”的日子,过年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我却越来越怀念儿时那浓浓的年味。
儿时过年与现在不同,那股浓浓的年味刚进腊月门便能感受到。当然,那时一切好像都是跟吃有关的。
上小学时,我们每年都是农历腊月廿一放假,正好第二天跟着爷爷去赶相州集。农历逢二排七是相州集,这事直到现在我也没忘。在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眼里,没有比相州集更热闹的地方了:各种各样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民间艺人纷纷登场。说书、唱戏的就不用说了,就连那些平时难得一见的捏面人、吹糖人、卖嘎吱虎的,也纷纷冒了出来。卖嘎吱虎的都是些外乡人,一听口音便知道。但直到长大后我才得知,这些嘎吱虎竟然有一个颇为高大上的名字——聂家庄泥塑,被誉为“高密三绝”之一,属于非遗。
最吸引我的还是卖吃食的那些摊点,柿饼、软枣、糖瓜是一定要买的,过小年时辞灶要用。至于卖糖葫芦的,我只看几眼便赶快把头扭开,尽管它们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此时我是绝对不会开口跟爷爷要的,因为我知道要也是白搭。爷爷宁肯花两毛钱让我吃顿炉包,也不舍得掏五分钱给我买串糖葫芦,这事曾让我困惑不已。快晌午了,爷爷会领我去紧邻相州饭店的老汤锅那儿,喝碗老汤。所谓“老汤”,是一碗盛在泥瓦盆里的羊杂汤,上面撒一点芫荽末,泡上玉米煎饼,边吃边喝。较之这东西,我更喜欢饭店里的炉包。这时,爷爷便会很慷慨地买上几个,让我打打牙祭,他自己却一个也不舍得吃。炉包那焦黄的嘎渣儿刺激着我的味蕾,咬一口,油香四溢。如今再怎么好吃的炉包,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腊月廿三,过小年。那天,母亲照例要全副武装地大扫除,然后晚上要吃水饺,祭灶。这时,我们头一天买的甜食便派上了用场。这些东西要等辞灶结束后才能分享,之前只能眼巴巴地瞅着。“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顶新毡帽”,这句谚语便生动地道出了我们北方过年时的一些习俗。
随后几天,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做豆腐、蒸饽饽、煮肉等,豆香、馍香、肉香交织在一起,氤氲在村庄的上空,汇聚成一股特有的年味。
儿时过年对孩子们来说,是真心地盼,发自内心地乐。对大人来说,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如今,我们早就过上了“天天十五月月年”的日子,过年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我却越来越怀念儿时那浓浓的年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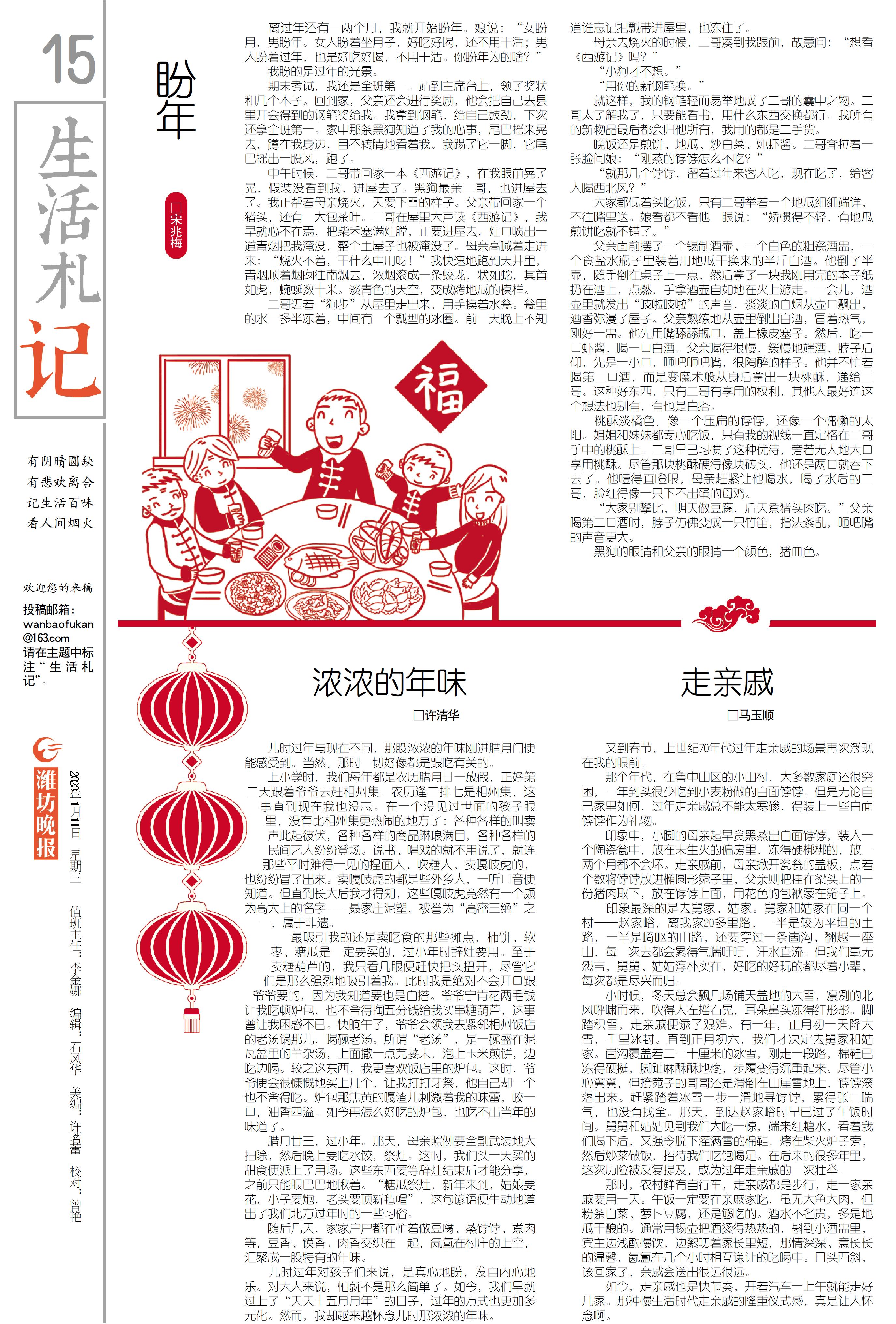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08 09/08 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111/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