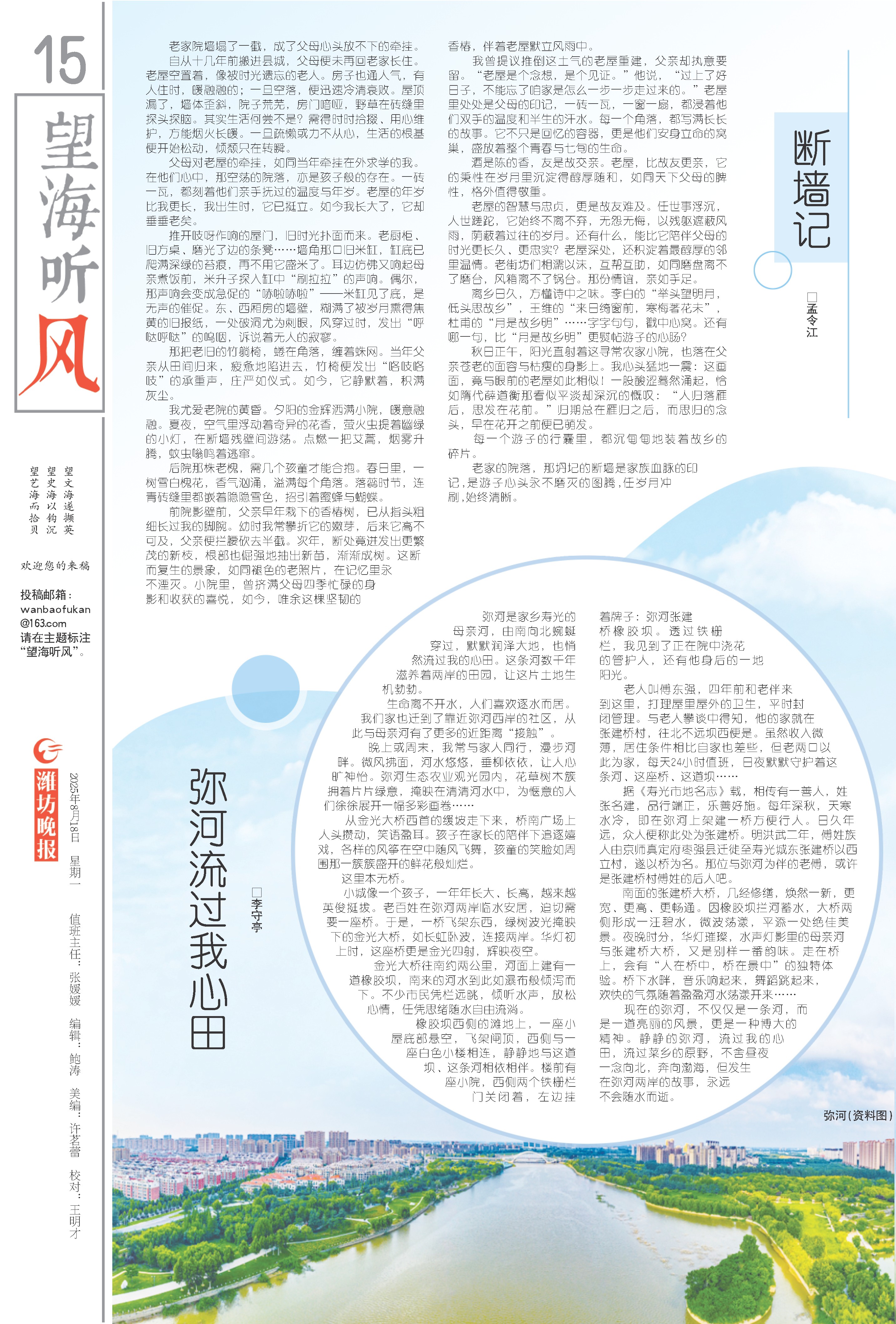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绿雾中的身影
□孟令江
老家院墙塌了一截,成了父母心头放不下的牵挂。
自从十几年前搬进县城,父母便未再回老家长住。老屋空置着,像被时光遗忘的老人。房子也通人气,有人住时,暖融融的;一旦空落,便迅速冷清衰败。屋顶漏了,墙体歪斜,院子荒芜,房门喑哑,野草在砖缝里探头探脑。其实生活何尝不是?需得时时拾掇、用心维护,方能烟火长暖。一旦疏懒或力不从心,生活的根基便开始松动,倾颓只在转瞬。
父母对老屋的牵挂,如同当年牵挂在外求学的我。在他们心中,那空荡的院落,亦是孩子般的存在。一砖一瓦,都刻着他们亲手抚过的温度与年岁。老屋的年岁比我更长,我出生时,它已挺立。如今我长大了,它却垂垂老矣。
推开吱呀作响的屋门,旧时光扑面而来。老厨柜、旧方桌、磨光了边的条凳……墙角那口旧米缸,缸底已爬满深绿的苔痕,再不用它盛米了。耳边仿佛又响起母亲煮饭前,米升子探入缸中“刷拉拉”的声响。偶尔,那声响会变成急促的“哧啦哧啦”——米缸见了底,是无声的催促。东、西厢房的墙壁,糊满了被岁月熏得焦黄的旧报纸,一处破洞尤为刺眼,风穿过时,发出“呼哒呼哒”的呜咽,诉说着无人的寂寥。
那把老旧的竹躺椅,蜷在角落,缠着蛛网。当年父亲从田间归来,疲惫地陷进去,竹椅便发出“咯吱咯吱”的承重声,庄严如仪式。如今,它静默着,积满灰尘。
我尤爱老院的黄昏。夕阳的金辉洒满小院,暖意融融。夏夜,空气里浮动着奇异的花香,萤火虫提着幽绿的小灯,在断墙残壁间游荡。点燃一把艾蒿,烟雾升腾,蚊虫嗡鸣着逃窜。
后院那株老槐,需几个孩童才能合抱。春日里,一树雪白槐花,香气汹涌,溢满每个角落。落蕊时节,连青砖缝里都嵌着隐隐雪色,招引着蜜蜂与蝴蝶。
前院影壁前,父亲早年栽下的香椿树,已从指头粗细长过我的脚腕。幼时我常攀折它的嫩芽,后来它高不可及,父亲便拦腰砍去半截。次年,断处竟迸发出更繁茂的新枝,根部也倔强地抽出新苗,渐渐成树。这断而复生的景象,如同褪色的老照片,在记忆里永不湮灭。小院里,曾挤满父母四季忙碌的身影和收获的喜悦,如今,唯余这棵坚韧的香椿,伴着老屋默立风雨中。
我曾提议推倒这土气的老屋重建,父亲却执意要留。“老屋是个念想,是个见证。”他说,“过上了好日子,不能忘了咱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老屋里处处是父母的印记,一砖一瓦,一窗一扇,都浸着他们双手的温度和半生的汗水。每一个角落,都写满长长的故事。它不只是回忆的容器,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窝巢,盛放着整个青春与七旬的生命。
酒是陈的香,友是故交亲。老屋,比故友更亲,它的秉性在岁月里沉淀得醇厚随和,如同天下父母的脾性,格外值得敬重。
老屋的智慧与忠贞,更是故友难及。任世事浮沉,人世蹉跎,它始终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以残躯遮蔽风雨,荫蔽着过往的岁月。还有什么,能比它陪伴父母的时光更长久、更忠实?老屋深处,还积淀着最醇厚的邻里温情。老街坊们相濡以沫,互帮互助,如同磨盘离不了磨台,风箱离不了锅台。那份情谊,亲如手足。
离乡日久,方懂诗中之味。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的“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杜甫的“月是故乡明”……字字句句,戳中心窝。还有哪一句,比“月是故乡明”更熨帖游子的心肠?
秋日正午,阳光直射着这寻常农家小院,也落在父亲苍老的面容与枯瘦的身影上。我心头猛地一震:这画面,竟与眼前的老屋如此相似!一股酸涩蓦然涌起,恰如隋代薛道衡那看似平淡却深沉的慨叹:“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归期总在雁归之后,而思归的念头,早在花开之前便已萌发。
每一个游子的行囊里,都沉甸甸地装着故乡的碎片。
老家的院落,那坍圮的断墙是家族血脉的印记,是游子心头永不磨灭的图腾,任岁月冲刷,始终清晰。
老家院墙塌了一截,成了父母心头放不下的牵挂。
自从十几年前搬进县城,父母便未再回老家长住。老屋空置着,像被时光遗忘的老人。房子也通人气,有人住时,暖融融的;一旦空落,便迅速冷清衰败。屋顶漏了,墙体歪斜,院子荒芜,房门喑哑,野草在砖缝里探头探脑。其实生活何尝不是?需得时时拾掇、用心维护,方能烟火长暖。一旦疏懒或力不从心,生活的根基便开始松动,倾颓只在转瞬。
父母对老屋的牵挂,如同当年牵挂在外求学的我。在他们心中,那空荡的院落,亦是孩子般的存在。一砖一瓦,都刻着他们亲手抚过的温度与年岁。老屋的年岁比我更长,我出生时,它已挺立。如今我长大了,它却垂垂老矣。
推开吱呀作响的屋门,旧时光扑面而来。老厨柜、旧方桌、磨光了边的条凳……墙角那口旧米缸,缸底已爬满深绿的苔痕,再不用它盛米了。耳边仿佛又响起母亲煮饭前,米升子探入缸中“刷拉拉”的声响。偶尔,那声响会变成急促的“哧啦哧啦”——米缸见了底,是无声的催促。东、西厢房的墙壁,糊满了被岁月熏得焦黄的旧报纸,一处破洞尤为刺眼,风穿过时,发出“呼哒呼哒”的呜咽,诉说着无人的寂寥。
那把老旧的竹躺椅,蜷在角落,缠着蛛网。当年父亲从田间归来,疲惫地陷进去,竹椅便发出“咯吱咯吱”的承重声,庄严如仪式。如今,它静默着,积满灰尘。
我尤爱老院的黄昏。夕阳的金辉洒满小院,暖意融融。夏夜,空气里浮动着奇异的花香,萤火虫提着幽绿的小灯,在断墙残壁间游荡。点燃一把艾蒿,烟雾升腾,蚊虫嗡鸣着逃窜。
后院那株老槐,需几个孩童才能合抱。春日里,一树雪白槐花,香气汹涌,溢满每个角落。落蕊时节,连青砖缝里都嵌着隐隐雪色,招引着蜜蜂与蝴蝶。
前院影壁前,父亲早年栽下的香椿树,已从指头粗细长过我的脚腕。幼时我常攀折它的嫩芽,后来它高不可及,父亲便拦腰砍去半截。次年,断处竟迸发出更繁茂的新枝,根部也倔强地抽出新苗,渐渐成树。这断而复生的景象,如同褪色的老照片,在记忆里永不湮灭。小院里,曾挤满父母四季忙碌的身影和收获的喜悦,如今,唯余这棵坚韧的香椿,伴着老屋默立风雨中。
我曾提议推倒这土气的老屋重建,父亲却执意要留。“老屋是个念想,是个见证。”他说,“过上了好日子,不能忘了咱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老屋里处处是父母的印记,一砖一瓦,一窗一扇,都浸着他们双手的温度和半生的汗水。每一个角落,都写满长长的故事。它不只是回忆的容器,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窝巢,盛放着整个青春与七旬的生命。
酒是陈的香,友是故交亲。老屋,比故友更亲,它的秉性在岁月里沉淀得醇厚随和,如同天下父母的脾性,格外值得敬重。
老屋的智慧与忠贞,更是故友难及。任世事浮沉,人世蹉跎,它始终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以残躯遮蔽风雨,荫蔽着过往的岁月。还有什么,能比它陪伴父母的时光更长久、更忠实?老屋深处,还积淀着最醇厚的邻里温情。老街坊们相濡以沫,互帮互助,如同磨盘离不了磨台,风箱离不了锅台。那份情谊,亲如手足。
离乡日久,方懂诗中之味。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的“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杜甫的“月是故乡明”……字字句句,戳中心窝。还有哪一句,比“月是故乡明”更熨帖游子的心肠?
秋日正午,阳光直射着这寻常农家小院,也落在父亲苍老的面容与枯瘦的身影上。我心头猛地一震:这画面,竟与眼前的老屋如此相似!一股酸涩蓦然涌起,恰如隋代薛道衡那看似平淡却深沉的慨叹:“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归期总在雁归之后,而思归的念头,早在花开之前便已萌发。
每一个游子的行囊里,都沉甸甸地装着故乡的碎片。
老家的院落,那坍圮的断墙是家族血脉的印记,是游子心头永不磨灭的图腾,任岁月冲刷,始终清晰。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18/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