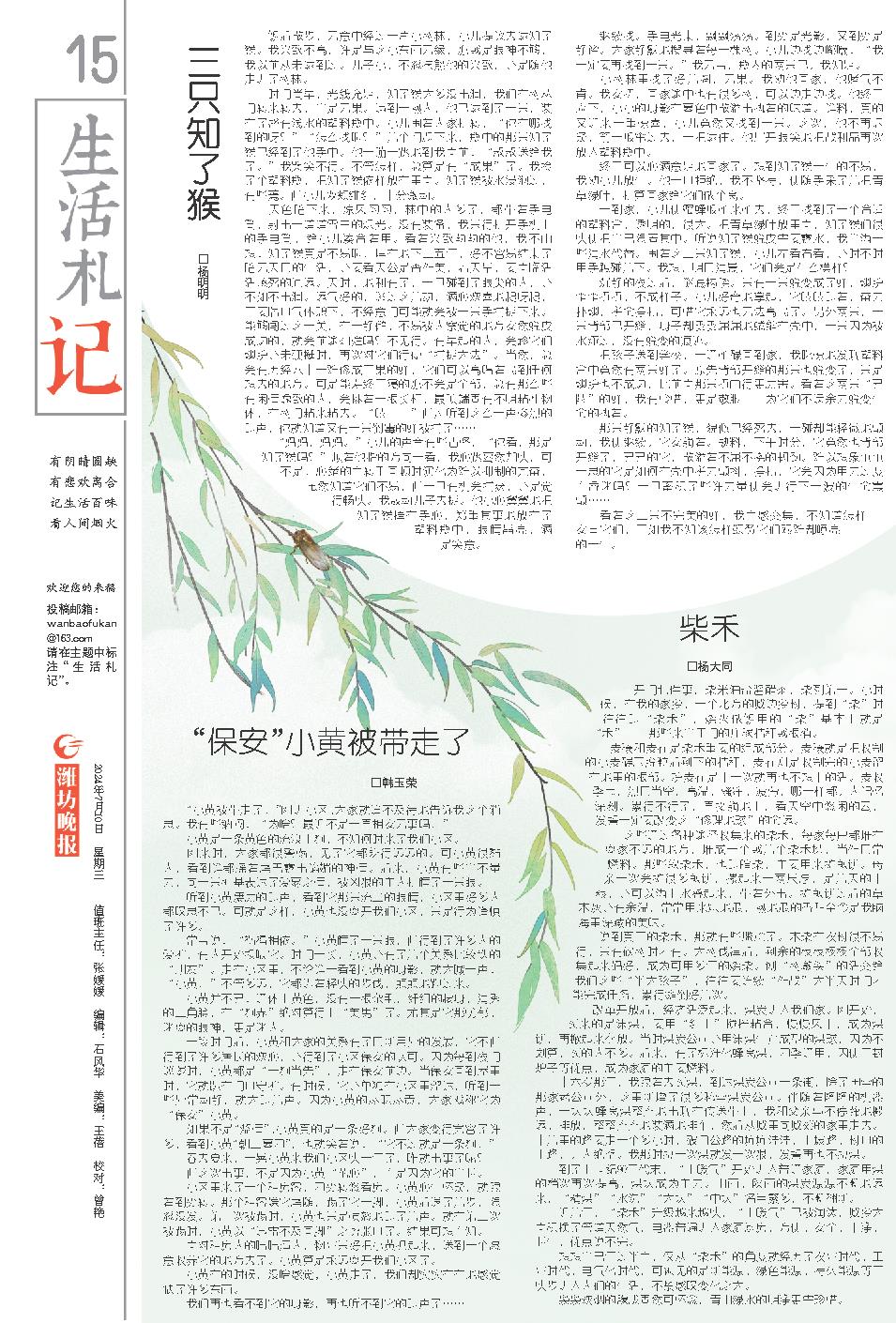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阅享暑假
 15版:生活札记
15版:生活札记
- * 三只知了猴
- * “保安”小黄被带走了
- * 柴禾
□杨大同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列第一。小时候,在我的家乡,一个北方的城边乡村,提到“柴”时往往叫“柴禾”,烧火做饭用的“柴”基本上就是“禾”——那些来自田间的庄稼秸秆或根梢。
麦穰和麦茬是柴禾重要的组成部分。麦穰就是把收割的小麦碾压脱粒后剩下的秸秆,麦茬则是收割完的小麦留在地里的根部。耪麦茬是干一次就再也不想干的活。麦收季节,烈日当空,高温、骚痒、疲劳,哪一样都让人记忆深刻。累得不行了,直接躺地上,看天空中悠闲的云,发誓一定要改变这“修理地球”的命运。
这些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来的柴禾,每家每户都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堆成一个或几个柴禾垛,当作日常燃料。那些软柴禾,也叫暄柴,主要用来摊煎饼。母亲一次会摊很多煎饼,摞起来一两尺厚,是几天的干粮,还可以洒上水叠起来,带着外出。摊煎饼过后的草木灰还有余温,常常用来烘地瓜,熟地瓜的香甜至今是我脑海里深藏的美味。
说到真正的柴禾,那就有些尴尬了。木柴在农村很不易得,只有砍树时才有。大树伐掉后,剩余的枝枝杈杈全部收集起来码好,成为可用多年的烧柴。刨“树墩头”的活交给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往往要连续“作战”大半天时间才能完成任务,累得瘫倒好几次。
改革开放后,经济活泛起来,煤炭进入我们家。刚开始,买来的是沫煤,要用“红土”搅拌粘合,慢慢风干,成为煤饼,再掀起来存放。当时煤炭公司还用沫煤生产成型的煤球,因为不划算,买的人不多。后来,有了标准化蜂窝煤,四季通用,因便于封炉子等优点,成为家庭的主要燃料。
十六岁那年,我跟着去买煤,到达煤炭公司一条街,除了国营的那家老公司外,这里新增了很多私营煤炭公司。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一块块蜂窝煤整齐地出现在传送带上,我和父亲马不停蹄地搬运、排放,整整齐齐地装满地排车,然后从城里向城郊的家里走去。十几里的路要走一个多小时,破旧公路的坑坑洼洼、上坡路、村口的土路,让人绝望。我那时拉一次煤就发一次狠,发誓再也不拉煤。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土暖气”开始进入普通家庭,家庭用煤的档次再次提高,煤块成为主力。山西、陕西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来,“精煤”“水洗”“大块”“中块”名目繁多,不断翻新。
近几年,“柴禾”升级越来越快,“土暖气”已被淘汰,城乡大面积换了管道天然气,电器普遍进入家庭厨房,方便、安全、干净、卫生,优点说不完。
想想自己年过半百,仅从“柴禾”的角度就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电气化时代,可预见的是新能源、绿色能源、持久能源等正快步进入人们的生活,不禁感叹变化之大。
袅袅炊烟的朦胧固然可怀念,青山绿水的明净更需珍惜。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列第一。小时候,在我的家乡,一个北方的城边乡村,提到“柴”时往往叫“柴禾”,烧火做饭用的“柴”基本上就是“禾”——那些来自田间的庄稼秸秆或根梢。
麦穰和麦茬是柴禾重要的组成部分。麦穰就是把收割的小麦碾压脱粒后剩下的秸秆,麦茬则是收割完的小麦留在地里的根部。耪麦茬是干一次就再也不想干的活。麦收季节,烈日当空,高温、骚痒、疲劳,哪一样都让人记忆深刻。累得不行了,直接躺地上,看天空中悠闲的云,发誓一定要改变这“修理地球”的命运。
这些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来的柴禾,每家每户都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堆成一个或几个柴禾垛,当作日常燃料。那些软柴禾,也叫暄柴,主要用来摊煎饼。母亲一次会摊很多煎饼,摞起来一两尺厚,是几天的干粮,还可以洒上水叠起来,带着外出。摊煎饼过后的草木灰还有余温,常常用来烘地瓜,熟地瓜的香甜至今是我脑海里深藏的美味。
说到真正的柴禾,那就有些尴尬了。木柴在农村很不易得,只有砍树时才有。大树伐掉后,剩余的枝枝杈杈全部收集起来码好,成为可用多年的烧柴。刨“树墩头”的活交给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往往要连续“作战”大半天时间才能完成任务,累得瘫倒好几次。
改革开放后,经济活泛起来,煤炭进入我们家。刚开始,买来的是沫煤,要用“红土”搅拌粘合,慢慢风干,成为煤饼,再掀起来存放。当时煤炭公司还用沫煤生产成型的煤球,因为不划算,买的人不多。后来,有了标准化蜂窝煤,四季通用,因便于封炉子等优点,成为家庭的主要燃料。
十六岁那年,我跟着去买煤,到达煤炭公司一条街,除了国营的那家老公司外,这里新增了很多私营煤炭公司。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一块块蜂窝煤整齐地出现在传送带上,我和父亲马不停蹄地搬运、排放,整整齐齐地装满地排车,然后从城里向城郊的家里走去。十几里的路要走一个多小时,破旧公路的坑坑洼洼、上坡路、村口的土路,让人绝望。我那时拉一次煤就发一次狠,发誓再也不拉煤。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土暖气”开始进入普通家庭,家庭用煤的档次再次提高,煤块成为主力。山西、陕西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来,“精煤”“水洗”“大块”“中块”名目繁多,不断翻新。
近几年,“柴禾”升级越来越快,“土暖气”已被淘汰,城乡大面积换了管道天然气,电器普遍进入家庭厨房,方便、安全、干净、卫生,优点说不完。
想想自己年过半百,仅从“柴禾”的角度就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电气化时代,可预见的是新能源、绿色能源、持久能源等正快步进入人们的生活,不禁感叹变化之大。
袅袅炊烟的朦胧固然可怀念,青山绿水的明净更需珍惜。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710/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