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乘梦启航
成都再见 - *
潍坊人贴秋膘
绝密指南发布 - *
八段锦少年拳
来报名免费学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乘风破浪
□高玉宝
去福建,第一夜是在芜湖国道旁的一家旅馆住的,家庭旅馆,小格子间。
离目的地尚有一千多公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又困又乏,进了房间就往床上倒,被子是湿的,不是潮,是湿,好像刚洗过。只好和衣而眠,空调根本不起作用,在被窝里直发抖。同伴本想一路开车过去,三十几个小时,想想头皮发麻,我想还是住一晚吧。
窗外的雨紧一阵、歇一阵,不知不觉中,睡着了,梦里依然在开车,动画片一样跳动。等动画片终于播完,被冻醒了,一看时间才两点多,更冷,赶紧起床。同伴也不言语,洗把脸,出门。尽管外面飘着雨,但似乎比床上暖和,车里就如天堂般温暖了。忽然想起前一夜出南京,过安徽马鞍山时是七点多钟,刚刚进芜湖,一个骑电动车的和一辆小汽车撞在了一起。电动车倒在地上,头盔掉了,露出一个小女孩的黄头发,地上一摊血,小女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同伴只是听我絮叨,专注开车。一路下雨,整整下了一千多公里,这样的事儿我也是头一次遇到。
到了目的地,已是夜里八点多,当地的朋友招呼吃饭。哪还有心情吃饭,只想倒头就睡。结果,提前预订的房间前台无人,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没人接,我们在小厅里吃板鸭,喝带来的啤酒,陆续几个朋友赶来,闽南话就是另一种语言,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觉得好玩,这语言如同唱歌,婉转、跳动,听不懂也听得入了迷。
这里曾生活过一代抗倭名将俞大猷,由俞大猷想起胡宗宪。他的第一个官职是益都(今山东青州)知县。七年后,他远赴浙江余姚任职,由青州到余姚,路线与我们此次出行有许多重叠。但1547年的出行和今天的出行相比,不再是一个概念了。胡宗宪,28岁步入官场,直到死于狱中,为官25年,因严嵩起,亦因严嵩倒,可悲。那时的文人既可提笔著述,又可提刀杀敌,俞家军、戚家军都与胡宗宪有关。这个安徽绩溪人,府上有一个著名的幕僚——徐渭,浙江绍兴人,他曾助胡宗宪擒徐海、诱汪直,在抗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徐渭,字画一流,文章一流,戏曲一流,军事亦懂,奇才。徐渭的故居我去过,在一个临河的小巷里,藏于闹市之中,小窄门,地砖上长满青苔——当年再如何狂放,如今,谁的影子也不见了。
我们的目的地出产一种特别的茶,有点铁观音的味道,但带着一些铁锈味。想起来时路上看到的红色山体,直觉上就可以判断出这里土壤的含铁量很高。所以,建盏就产在这里。
说起建盏,当地人会提到赵佶,当然是讲他如何喜爱建盏,用来斗茶。但是,他们不说他被掳一事,也不谈他是瘦金体的创始人,更不说他的画。赵佶不过是当地人用来宣传的手段,当然无需讲蔡京和《水浒传》,更别说《金瓶梅》,历史确实不过是一场过往,再繁花似锦,再空前绝后,再凄美如斯,不过云烟一场,抵不过人们介绍你买一把好盏的兴趣。
本地人喝茶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因为我不懂,不敢多说。他们泡茶用盖碗,再用公道杯,再用小勺给你“淋”茶,淋到牛眼小杯子里。我禁不住起敬,因为同伴说:“像小时候家里穷,大人用小勺子给我们分糖水喝。”忽然觉得,也许就是这个道理。端起杯子,让我这样的粗人也会想起大观园里妙玉对茶的见解,看来,我们与古人在文化上的差异真不是一星半点。用来喝茶的杯子小得不能再小,越小越精致,手绘、羊脂玉瓷,端在手里羽毛一样轻,像一件被赋予了生命的器物。
第二天依旧下雨,在路边小店买了一把伞,打着伞上山。山脚下的溪水浑浊,哗哗有声,向山下看去,落差很大,百十米高,如果纵身一跳,下面的小溪接不住任何人的重量。不敢再向下望,只靠近崖壁的那一侧前行。在峭壁上,看到一棵剑兰,长得修长,美人的秀发一样垂落在山体之上。应该是开白花的。我以前在书房养了一棵幽兰,开小花,满室幽香,真奇怪那么小、米粒大的花,哪来那么大的香气。兰花是朋友送的,说是从福建的山上自己挖回来的。我很珍惜,结果开了花后,就慢慢枯了。这事我惋惜了好多年,一直觉得,如果去福建,一定到山上去挖些回来,也要送给朋友们。可惜这些天一直下雨,山路湿滑,不敢贸然上山。
下山,雨差不多停了。南方的天气也神奇,雨,说下就下,说停就停。收了伞,迎面一个穿了蓑衣的老太太,弯腰挑着一个小小的竹担,小筐里放了几把蘑菇。我好奇,随手翻了一下。老人说自己80岁了,在山上采了点蘑菇,一小袋50块,不贵。我根本不认识那种蘑菇,觉得她肯挑出来卖,不会吃死人,就买了一袋。到朋友处,他们大笑,说那老太太很精明,不知从哪里买来的假蘑菇,挑出来专门卖给我这样的外地人。我也笑,想这不过是老人的生存手段,不算上当受骗。
去福建,第一夜是在芜湖国道旁的一家旅馆住的,家庭旅馆,小格子间。
离目的地尚有一千多公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又困又乏,进了房间就往床上倒,被子是湿的,不是潮,是湿,好像刚洗过。只好和衣而眠,空调根本不起作用,在被窝里直发抖。同伴本想一路开车过去,三十几个小时,想想头皮发麻,我想还是住一晚吧。
窗外的雨紧一阵、歇一阵,不知不觉中,睡着了,梦里依然在开车,动画片一样跳动。等动画片终于播完,被冻醒了,一看时间才两点多,更冷,赶紧起床。同伴也不言语,洗把脸,出门。尽管外面飘着雨,但似乎比床上暖和,车里就如天堂般温暖了。忽然想起前一夜出南京,过安徽马鞍山时是七点多钟,刚刚进芜湖,一个骑电动车的和一辆小汽车撞在了一起。电动车倒在地上,头盔掉了,露出一个小女孩的黄头发,地上一摊血,小女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同伴只是听我絮叨,专注开车。一路下雨,整整下了一千多公里,这样的事儿我也是头一次遇到。
到了目的地,已是夜里八点多,当地的朋友招呼吃饭。哪还有心情吃饭,只想倒头就睡。结果,提前预订的房间前台无人,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没人接,我们在小厅里吃板鸭,喝带来的啤酒,陆续几个朋友赶来,闽南话就是另一种语言,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觉得好玩,这语言如同唱歌,婉转、跳动,听不懂也听得入了迷。
这里曾生活过一代抗倭名将俞大猷,由俞大猷想起胡宗宪。他的第一个官职是益都(今山东青州)知县。七年后,他远赴浙江余姚任职,由青州到余姚,路线与我们此次出行有许多重叠。但1547年的出行和今天的出行相比,不再是一个概念了。胡宗宪,28岁步入官场,直到死于狱中,为官25年,因严嵩起,亦因严嵩倒,可悲。那时的文人既可提笔著述,又可提刀杀敌,俞家军、戚家军都与胡宗宪有关。这个安徽绩溪人,府上有一个著名的幕僚——徐渭,浙江绍兴人,他曾助胡宗宪擒徐海、诱汪直,在抗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徐渭,字画一流,文章一流,戏曲一流,军事亦懂,奇才。徐渭的故居我去过,在一个临河的小巷里,藏于闹市之中,小窄门,地砖上长满青苔——当年再如何狂放,如今,谁的影子也不见了。
我们的目的地出产一种特别的茶,有点铁观音的味道,但带着一些铁锈味。想起来时路上看到的红色山体,直觉上就可以判断出这里土壤的含铁量很高。所以,建盏就产在这里。
说起建盏,当地人会提到赵佶,当然是讲他如何喜爱建盏,用来斗茶。但是,他们不说他被掳一事,也不谈他是瘦金体的创始人,更不说他的画。赵佶不过是当地人用来宣传的手段,当然无需讲蔡京和《水浒传》,更别说《金瓶梅》,历史确实不过是一场过往,再繁花似锦,再空前绝后,再凄美如斯,不过云烟一场,抵不过人们介绍你买一把好盏的兴趣。
本地人喝茶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因为我不懂,不敢多说。他们泡茶用盖碗,再用公道杯,再用小勺给你“淋”茶,淋到牛眼小杯子里。我禁不住起敬,因为同伴说:“像小时候家里穷,大人用小勺子给我们分糖水喝。”忽然觉得,也许就是这个道理。端起杯子,让我这样的粗人也会想起大观园里妙玉对茶的见解,看来,我们与古人在文化上的差异真不是一星半点。用来喝茶的杯子小得不能再小,越小越精致,手绘、羊脂玉瓷,端在手里羽毛一样轻,像一件被赋予了生命的器物。
第二天依旧下雨,在路边小店买了一把伞,打着伞上山。山脚下的溪水浑浊,哗哗有声,向山下看去,落差很大,百十米高,如果纵身一跳,下面的小溪接不住任何人的重量。不敢再向下望,只靠近崖壁的那一侧前行。在峭壁上,看到一棵剑兰,长得修长,美人的秀发一样垂落在山体之上。应该是开白花的。我以前在书房养了一棵幽兰,开小花,满室幽香,真奇怪那么小、米粒大的花,哪来那么大的香气。兰花是朋友送的,说是从福建的山上自己挖回来的。我很珍惜,结果开了花后,就慢慢枯了。这事我惋惜了好多年,一直觉得,如果去福建,一定到山上去挖些回来,也要送给朋友们。可惜这些天一直下雨,山路湿滑,不敢贸然上山。
下山,雨差不多停了。南方的天气也神奇,雨,说下就下,说停就停。收了伞,迎面一个穿了蓑衣的老太太,弯腰挑着一个小小的竹担,小筐里放了几把蘑菇。我好奇,随手翻了一下。老人说自己80岁了,在山上采了点蘑菇,一小袋50块,不贵。我根本不认识那种蘑菇,觉得她肯挑出来卖,不会吃死人,就买了一袋。到朋友处,他们大笑,说那老太太很精明,不知从哪里买来的假蘑菇,挑出来专门卖给我这样的外地人。我也笑,想这不过是老人的生存手段,不算上当受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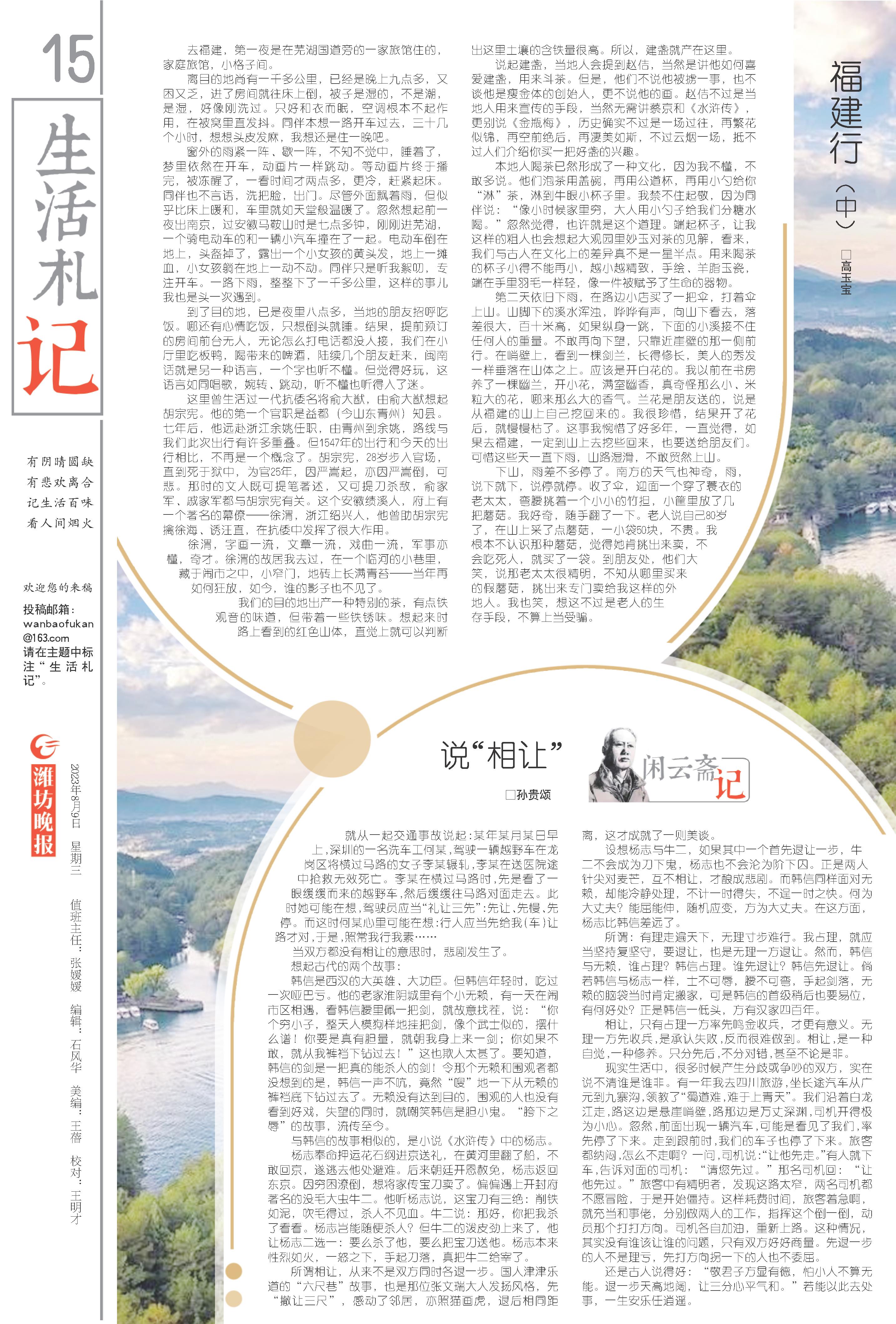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809/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