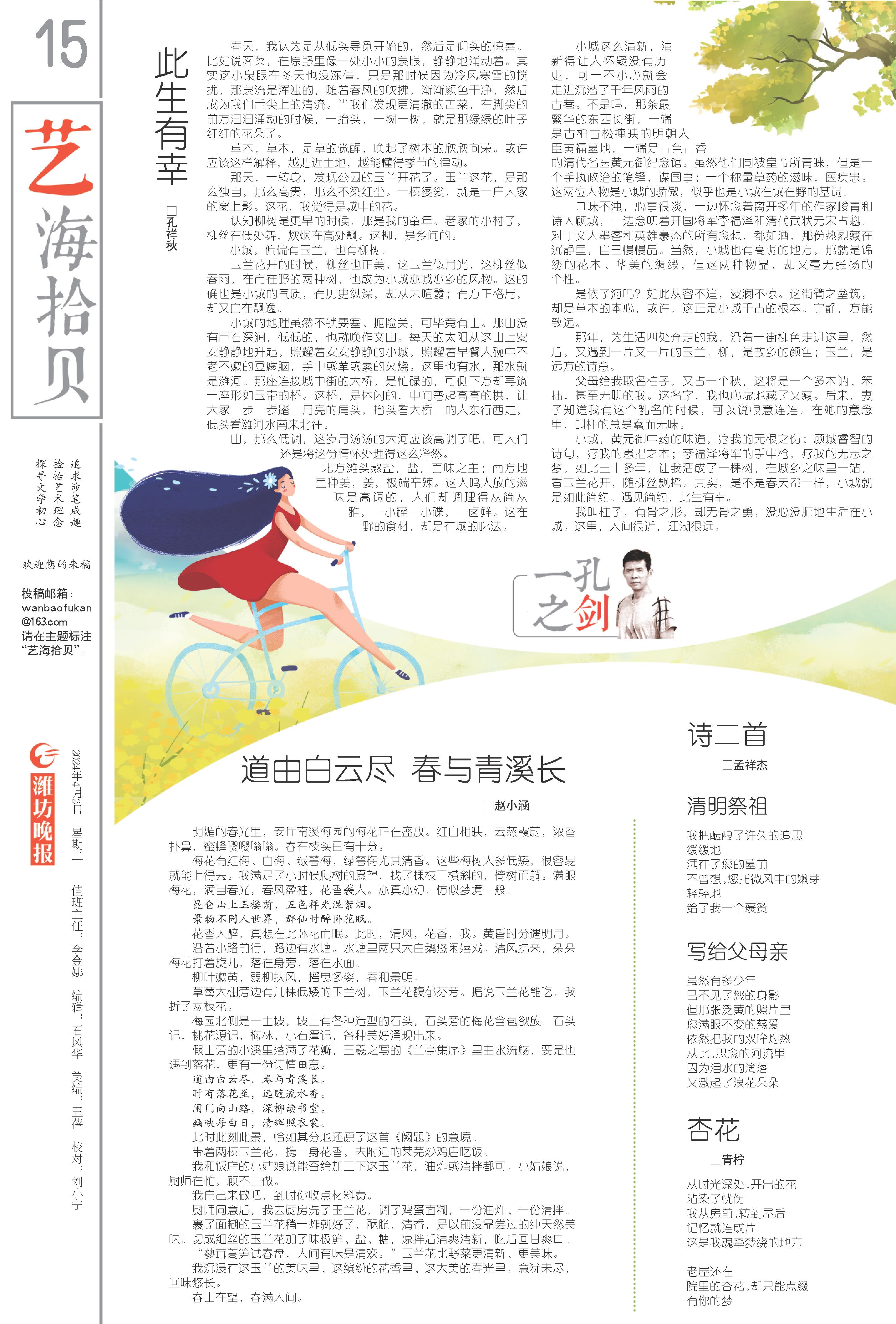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共植“思乡林”
 07版:我们的节日·清明
07版:我们的节日·清明
- * 清明假期出行 购票攻略请收好
- * 缅怀先烈学感恩
- * 多彩民俗迎清明
- * 文明祭扫寄哀思
 15版:艺海拾贝
15版:艺海拾贝
- * 此生有幸
- * 道由白云尽 春与青溪长
- * 诗二首
- * 杏花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花神驾到
□孔祥秋
春天,我认为是从低头寻觅开始的,然后是仰头的惊喜。比如说荠菜,在原野里像一处小小的泉眼,静静地涌动着。其实这小泉眼在冬天也没冻僵,只是那时候因为冷风寒雪的搅扰,那泉流是浑浊的,随着春风的吹拂,渐渐颜色干净,然后成为我们舌尖上的清流。当我们发现更清澈的苦菜,在脚尖的前方汩汩涌动的时候,一抬头,一树一树,就是那绿绿的叶子红红的花朵了。
草木,草木,是草的觉醒,唤起了树木的欣欣向荣。或许应该这样解释,越贴近土地,越能懂得季节的律动。
那天,一转身,发现公园的玉兰开花了。玉兰这花,是那么独自,那么高贵,那么不染红尘。一枝婆娑,就是一户人家的窗上影。这花,我觉得是城中的花。
认知柳树是更早的时候,那是我的童年。老家的小村子,柳丝在低处舞,炊烟在高处飘。这柳,是乡间的。
小城,偏偏有玉兰,也有柳树。
玉兰花开的时候,柳丝也正美,这玉兰似月光,这柳丝似春雨,在市在野的两种树,也成为小城亦城亦乡的风物。这的确也是小城的气质,有历史纵深,却从未喧嚣;有方正格局,却又自在飘逸。
小城的地理虽然不锁要塞、扼险关,可毕竟有山。那山没有巨石深涧,低低的,也就唤作文山。每天的太阳从这山上安安静静地升起,照耀着安安静静的小城,照耀着早餐人碗中不老不嫩的豆腐脑,手中或荤或素的火烧。这里也有水,那水就是潍河。那座连接城中街的大桥,是忙碌的,可侧下方却再筑一座形如玉带的桥。这桥,是休闲的,中间弯起高高的拱,让大家一步一步踏上月亮的肩头,抬头看大桥上的人东行西走,低头看潍河水南来北往。
山,那么低调,这岁月汤汤的大河应该高调了吧,可人们还是将这份情怀处理得这么释然。
北方滩头熬盐,盐,百味之主;南方地里种姜,姜,极端辛辣。这大鸣大放的滋味是高调的,人们却调理得从简从雅,一小罐一小碟,一卤鲜。这在野的食材,却是在城的吃法。
小城这么清新,清新得让人怀疑没有历史,可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沉潜了千年风雨的古巷。不是吗,那条最繁华的东西长街,一端是古柏古松掩映的明朝大臣黄福墓地,一端是古色古香的清代名医黄元御纪念馆。虽然他们同被皇帝所青睐,但是一个手执政治的笔锋,谋国事;一个称量草药的滋味,医疾患。这两位人物是小城的骄傲,似乎也是小城在城在野的基调。
口味不浊,心事很淡,一边怀念着离开多年的作家峻青和诗人顾城,一边念叨着开国将军李福泽和清代武状元宋占魁。对于文人墨客和英雄豪杰的所有念想,都如酒,那份热烈藏在沉静里,自己慢慢品。当然,小城也有高调的地方,那就是锦绣的花木、华美的绸缎,但这两种物品,却又毫无张扬的个性。
是依了海吗?如此从容不迫,波澜不惊。这街衢之垒筑,却是草木的本心,或许,这正是小城千古的根本。宁静,方能致远。
那年,为生活四处奔走的我,沿着一街柳色走进这里,然后,又遇到一片又一片的玉兰。柳,是故乡的颜色;玉兰,是远方的诗意。
父母给我取名柱子,又占一个秋,这将是一个多木讷、笨拙,甚至无聊的我。这名字,我也心虚地藏了又藏。后来,妻子知道我有这个乳名的时候,可以说恨意连连。在她的意念里,叫柱的总是蠢而无味。
小城,黄元御中药的味道,疗我的无根之伤;顾城睿智的诗句,疗我的愚拙之本;李福泽将军的手中枪,疗我的无志之梦,如此三十多年,让我活成了一棵树,在城乡之味里一站,看玉兰花开,随柳丝飘摇。其实,是不是春天都一样,小城就是如此简约。遇见简约,此生有幸。
我叫柱子,有骨之形,却无骨之勇,没心没肺地生活在小城。这里,人间很近,江湖很远。
春天,我认为是从低头寻觅开始的,然后是仰头的惊喜。比如说荠菜,在原野里像一处小小的泉眼,静静地涌动着。其实这小泉眼在冬天也没冻僵,只是那时候因为冷风寒雪的搅扰,那泉流是浑浊的,随着春风的吹拂,渐渐颜色干净,然后成为我们舌尖上的清流。当我们发现更清澈的苦菜,在脚尖的前方汩汩涌动的时候,一抬头,一树一树,就是那绿绿的叶子红红的花朵了。
草木,草木,是草的觉醒,唤起了树木的欣欣向荣。或许应该这样解释,越贴近土地,越能懂得季节的律动。
那天,一转身,发现公园的玉兰开花了。玉兰这花,是那么独自,那么高贵,那么不染红尘。一枝婆娑,就是一户人家的窗上影。这花,我觉得是城中的花。
认知柳树是更早的时候,那是我的童年。老家的小村子,柳丝在低处舞,炊烟在高处飘。这柳,是乡间的。
小城,偏偏有玉兰,也有柳树。
玉兰花开的时候,柳丝也正美,这玉兰似月光,这柳丝似春雨,在市在野的两种树,也成为小城亦城亦乡的风物。这的确也是小城的气质,有历史纵深,却从未喧嚣;有方正格局,却又自在飘逸。
小城的地理虽然不锁要塞、扼险关,可毕竟有山。那山没有巨石深涧,低低的,也就唤作文山。每天的太阳从这山上安安静静地升起,照耀着安安静静的小城,照耀着早餐人碗中不老不嫩的豆腐脑,手中或荤或素的火烧。这里也有水,那水就是潍河。那座连接城中街的大桥,是忙碌的,可侧下方却再筑一座形如玉带的桥。这桥,是休闲的,中间弯起高高的拱,让大家一步一步踏上月亮的肩头,抬头看大桥上的人东行西走,低头看潍河水南来北往。
山,那么低调,这岁月汤汤的大河应该高调了吧,可人们还是将这份情怀处理得这么释然。
北方滩头熬盐,盐,百味之主;南方地里种姜,姜,极端辛辣。这大鸣大放的滋味是高调的,人们却调理得从简从雅,一小罐一小碟,一卤鲜。这在野的食材,却是在城的吃法。
小城这么清新,清新得让人怀疑没有历史,可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沉潜了千年风雨的古巷。不是吗,那条最繁华的东西长街,一端是古柏古松掩映的明朝大臣黄福墓地,一端是古色古香的清代名医黄元御纪念馆。虽然他们同被皇帝所青睐,但是一个手执政治的笔锋,谋国事;一个称量草药的滋味,医疾患。这两位人物是小城的骄傲,似乎也是小城在城在野的基调。
口味不浊,心事很淡,一边怀念着离开多年的作家峻青和诗人顾城,一边念叨着开国将军李福泽和清代武状元宋占魁。对于文人墨客和英雄豪杰的所有念想,都如酒,那份热烈藏在沉静里,自己慢慢品。当然,小城也有高调的地方,那就是锦绣的花木、华美的绸缎,但这两种物品,却又毫无张扬的个性。
是依了海吗?如此从容不迫,波澜不惊。这街衢之垒筑,却是草木的本心,或许,这正是小城千古的根本。宁静,方能致远。
那年,为生活四处奔走的我,沿着一街柳色走进这里,然后,又遇到一片又一片的玉兰。柳,是故乡的颜色;玉兰,是远方的诗意。
父母给我取名柱子,又占一个秋,这将是一个多木讷、笨拙,甚至无聊的我。这名字,我也心虚地藏了又藏。后来,妻子知道我有这个乳名的时候,可以说恨意连连。在她的意念里,叫柱的总是蠢而无味。
小城,黄元御中药的味道,疗我的无根之伤;顾城睿智的诗句,疗我的愚拙之本;李福泽将军的手中枪,疗我的无志之梦,如此三十多年,让我活成了一棵树,在城乡之味里一站,看玉兰花开,随柳丝飘摇。其实,是不是春天都一样,小城就是如此简约。遇见简约,此生有幸。
我叫柱子,有骨之形,却无骨之勇,没心没肺地生活在小城。这里,人间很近,江湖很远。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2/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