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版:公益广告
10版:公益广告
- * 公益广告
 15版:生活札记
15版:生活札记
- * 消失的姓氏与模糊的辈分
- * 至乐莫如读书
- * 故乡 艾蒿 童年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夏日迷人瞬间
□孙贵颂
在云南丽江的傈僳族中,有一支以鸟为图腾的家族,姓“nià”(“nià”字上半部分是少了一横的“鸟”,下半部分是“甲”)。
后来,“nià”姓村民在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因为电脑里没有这个字,系统识别不了,只好将其拆开,分为左“甲”右“鸟”,组成了鸭子的“鸭”。“村里姓‘nià’的都改成姓‘鸭’了。遗憾也没有用,不改就没法外出,甚至卡里的钱都没法提现。”
傈僳族讲究氏族文化,崇拜动植物。姓“nià”的村民说,他们是鸟氏族的后代,那种鸟长得像鹰隼,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庇护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是如今改成“鸭”后,便由本来翱翔于天空的飞鸟,沦为了地上行走的家禽。虽然不情愿,但也没办法。
图腾也随之消失了。
我思绪跑马,觉得姓氏这种有着极强血脉与文化传承的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中国有逐渐淡化的趋势,值得讨论与警惕。
我有个朋友,原来姓李,后来他以其家乡一座山的名字,起名云龙子。再后来,又将儿子的姓改成云龙,成了一个新复姓。现在这个复姓已赫然出现在公安局颁发的户口簿上,合法了。这说明,姓氏确实允许变动。
日前遇到一位孔姓朋友,我问他:“你们孔家现在传到多少代了?”他告诉我:“已经到83代了。”除了孔氏,还有孟氏,从春秋战国开始至今,历经2500多年,一直瓜瓞绵绵,继往开来,生生不息。
除了孔孟,这样的家族委实不多。
孔孟的后代,在孩子出生时,绝大多数按照其家谱字辈的排序来起名字。而另外绝大多数姓氏的家庭,这样遵循的家长渐渐稀少。男孩就叫泰星、青云、英鸿、博瀚、骏月……女孩就叫雪枫、雅冉、思蝶、荷月、静美……做了父母的年轻一代,不太关心其家谱字辈,也不想去承续那个家谱字辈。这种现象,表面看来是忽视辈分序列,实际上是家族情感淡化所致。
现今的青年很多是独生子女,往往只与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有来往。即使有堂兄弟、堂姐妹或表兄弟、表姐妹,也往往比较生疏,远不如同学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亲密。友情关系大大超过了血统关系。他们对家族成员的婚丧嫁娶、建厂盖房等重大事件漠不关心,反而在同学、朋友娶妻生子、贷款购车等事情上予以援手或关爱。在南来北往的流动中,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问到对方姓甚名谁时,碰到一个与自己同姓的人,常会说:“咱们500年前是一家啊!”甚至会论论亲、排排辈,哪怕一个在海南,一个居河北。而如果年轻人凑到一起遇到这种情况,根本不会说在他们看来有点迂腐的话题。
忽然想到一些名人。
假如有人在高中生和大学生之外,对公众进行一番考试,有谁知道鲁迅、老舍、冰心姓甚名谁?有谁知道金庸、古龙、梁羽生原来叫什么名字?让我悄悄地告诉你:前面几位分别是周树人、舒庆春、谢婉莹,后面几位分别是查良镛、熊耀华、陈文统。这些人均是以笔名驰誉文坛,而其真名被本人与读者所忽略。
当家族的姓氏不重要了、辈分不重要了,一个人的姓名倒真的成了一个代码或符号,叫什么就显得无伤大雅了。
文章要结束时,忽然从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一位从事亲子鉴定十几年的医生爆料:在北方某省,从2019年到2021年,每100个去做亲子鉴定的人,有90.57%的概率不是亲生的。也就是说,亲生的只占约10%。你看,这些人虽然拥有姓氏与辈分,但却不存在血缘关系了。
在云南丽江的傈僳族中,有一支以鸟为图腾的家族,姓“nià”(“nià”字上半部分是少了一横的“鸟”,下半部分是“甲”)。
后来,“nià”姓村民在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因为电脑里没有这个字,系统识别不了,只好将其拆开,分为左“甲”右“鸟”,组成了鸭子的“鸭”。“村里姓‘nià’的都改成姓‘鸭’了。遗憾也没有用,不改就没法外出,甚至卡里的钱都没法提现。”
傈僳族讲究氏族文化,崇拜动植物。姓“nià”的村民说,他们是鸟氏族的后代,那种鸟长得像鹰隼,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庇护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是如今改成“鸭”后,便由本来翱翔于天空的飞鸟,沦为了地上行走的家禽。虽然不情愿,但也没办法。
图腾也随之消失了。
我思绪跑马,觉得姓氏这种有着极强血脉与文化传承的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中国有逐渐淡化的趋势,值得讨论与警惕。
我有个朋友,原来姓李,后来他以其家乡一座山的名字,起名云龙子。再后来,又将儿子的姓改成云龙,成了一个新复姓。现在这个复姓已赫然出现在公安局颁发的户口簿上,合法了。这说明,姓氏确实允许变动。
日前遇到一位孔姓朋友,我问他:“你们孔家现在传到多少代了?”他告诉我:“已经到83代了。”除了孔氏,还有孟氏,从春秋战国开始至今,历经2500多年,一直瓜瓞绵绵,继往开来,生生不息。
除了孔孟,这样的家族委实不多。
孔孟的后代,在孩子出生时,绝大多数按照其家谱字辈的排序来起名字。而另外绝大多数姓氏的家庭,这样遵循的家长渐渐稀少。男孩就叫泰星、青云、英鸿、博瀚、骏月……女孩就叫雪枫、雅冉、思蝶、荷月、静美……做了父母的年轻一代,不太关心其家谱字辈,也不想去承续那个家谱字辈。这种现象,表面看来是忽视辈分序列,实际上是家族情感淡化所致。
现今的青年很多是独生子女,往往只与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有来往。即使有堂兄弟、堂姐妹或表兄弟、表姐妹,也往往比较生疏,远不如同学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亲密。友情关系大大超过了血统关系。他们对家族成员的婚丧嫁娶、建厂盖房等重大事件漠不关心,反而在同学、朋友娶妻生子、贷款购车等事情上予以援手或关爱。在南来北往的流动中,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问到对方姓甚名谁时,碰到一个与自己同姓的人,常会说:“咱们500年前是一家啊!”甚至会论论亲、排排辈,哪怕一个在海南,一个居河北。而如果年轻人凑到一起遇到这种情况,根本不会说在他们看来有点迂腐的话题。
忽然想到一些名人。
假如有人在高中生和大学生之外,对公众进行一番考试,有谁知道鲁迅、老舍、冰心姓甚名谁?有谁知道金庸、古龙、梁羽生原来叫什么名字?让我悄悄地告诉你:前面几位分别是周树人、舒庆春、谢婉莹,后面几位分别是查良镛、熊耀华、陈文统。这些人均是以笔名驰誉文坛,而其真名被本人与读者所忽略。
当家族的姓氏不重要了、辈分不重要了,一个人的姓名倒真的成了一个代码或符号,叫什么就显得无伤大雅了。
文章要结束时,忽然从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一位从事亲子鉴定十几年的医生爆料:在北方某省,从2019年到2021年,每100个去做亲子鉴定的人,有90.57%的概率不是亲生的。也就是说,亲生的只占约10%。你看,这些人虽然拥有姓氏与辈分,但却不存在血缘关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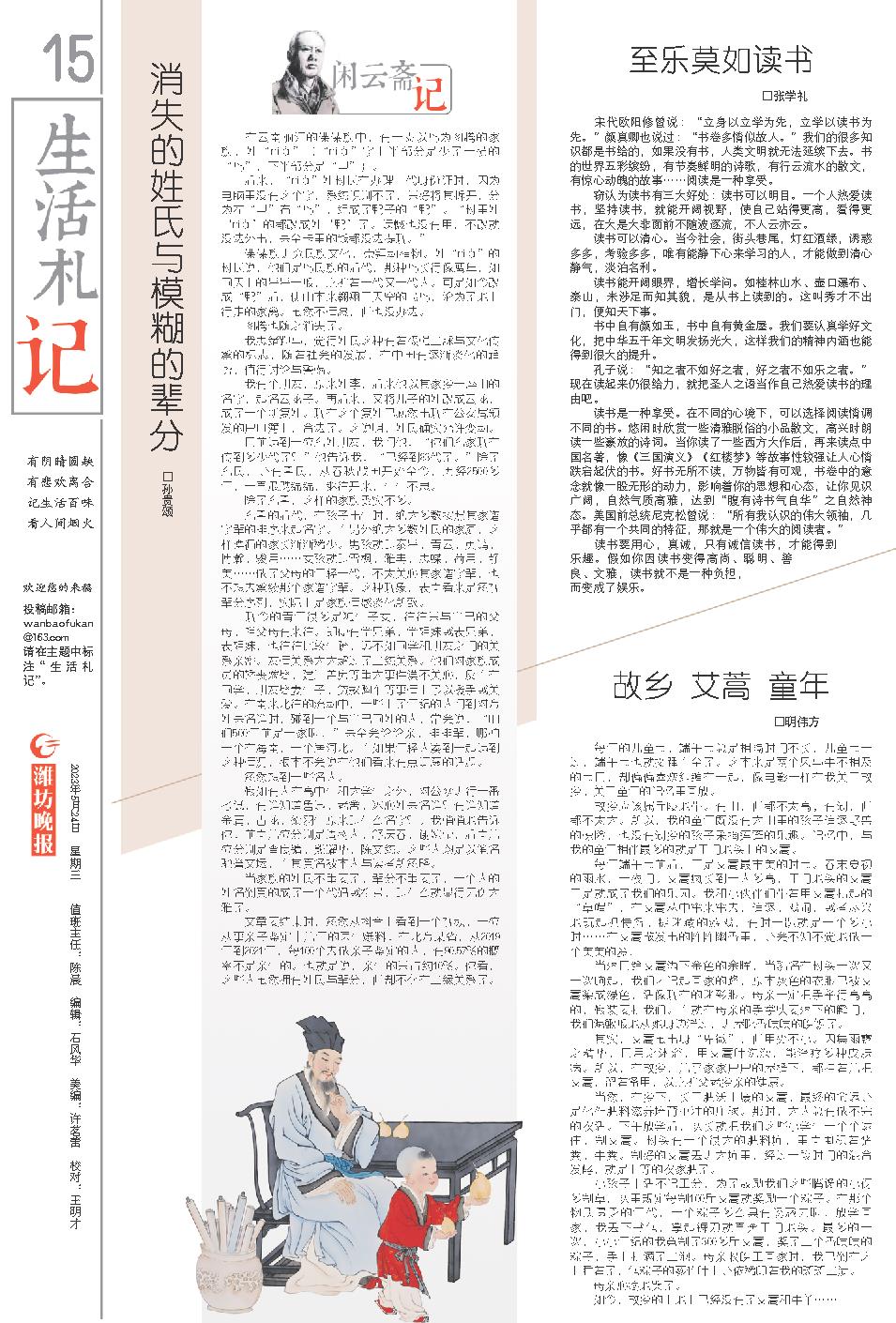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524/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