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版:都市新闻
04版:都市新闻
- * 找到了! 漏点在地下七米
- *
“全城亮屏”
请您安全回家 - *
安全通道
既结实又美观 - * 多遍消杀 让快件安全到家
- *
督导整治
共享单车乱象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白鹭和苍鹭
□孙朝晖
天高云淡,清风从土地上拂过,庄稼就开始成熟。大豆举着黄色的硬荚,里面的豆子在风中作响。玉米是揣着孩子的婆娘,左搂右抱,长叶披拂,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清风把我带到40年前的场院。生产队的场院,到处是一堆堆玉米,包裹着绿色的外皮,堆积如山。把玉米皮剥掉,晾晒入库,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需要动员各家各户。
剥玉米皮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劳动是有报酬的,玉米归集体,社员得到的是那些剥掉的外皮。玉米皮用途多多,晒干是很好的烧火材料。那些洁白柔软的内皮,晒干后可以铺在垫子上蒸馒头蒸窝头,蒸出来不易黏皮,而且味道香甜可口。
各家的全体成员早早吃过晚饭,拿着板凳马扎,三五成群,像是过节一样,走进场院里。他们坐在玉米堆里,撕掉玉米外面的硬皮,露出如蚱蜢内翅般的内皮,再将多数内皮撕掉,只留一两张,卷实,将两只剥好的玉米相对打个结,再将另一只剥好的玉米编上去。如此,一只一只地相接,像辫子一样编在一起,直到编成一条长龙,将黄澄澄的长龙搭在墙头或是挂在木桩上,便于晾晒。
夕阳斜照,场院里,大家都在大声说笑着。既为丰收欢喜,也为这些玉米皮兴奋。忙碌之间,夜幕展开,场院里亮起灯,人们都隐藏在一座座小山似的玉米堆里,双手在白色的皮衣上跳动。大家都在抓住这一年一次的机会,争取多挣一些玉米皮回家。
场院也是孩子们的天堂。他们玩闹着,在小山之间窜来窜去,追逐打闹捉迷藏。有的就地取材,撕一把黑色的玉米须,咬在嘴里,扮作京戏里的张飞刘备。有的将玉米秆去掉叶子,做成金箍棒,相互招架击打。有的在玉米秆前端插上两根小棍,当做机枪,嘴里还嘟嘟着,像在射出子弹。玩闹够了,孩子们也会干活。他们不会编玉米,却会把那些小的不能入编的玉米直接剥掉外皮扔在大堆里。
夜色深了,月亮升到半空。场院里安静下来,蟋蟀的叫声此起彼伏,雾气开始弥漫,绿色的小山慢慢地变矮消失,成为一个个闪闪发黄的丘陵。人们在薄薄的雾气里浮现,一条条黄澄澄的长龙在脚下蜿蜒开来。
我又累又困,人影和虫声似乎远去了,却又觉得身体在晃动,像是躺在摇摆的秋千上。我睁开眼睛,发现那轮明月正挂在头顶上,向我微微地轻笑。原来,我睡在了独轮小车上,父亲正推着我往家走。车上堆满了绵软的玉米皮,母亲、姐姐一起在后面走着,疲惫而喜悦。
天高云淡,清风从土地上拂过,庄稼就开始成熟。大豆举着黄色的硬荚,里面的豆子在风中作响。玉米是揣着孩子的婆娘,左搂右抱,长叶披拂,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清风把我带到40年前的场院。生产队的场院,到处是一堆堆玉米,包裹着绿色的外皮,堆积如山。把玉米皮剥掉,晾晒入库,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需要动员各家各户。
剥玉米皮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劳动是有报酬的,玉米归集体,社员得到的是那些剥掉的外皮。玉米皮用途多多,晒干是很好的烧火材料。那些洁白柔软的内皮,晒干后可以铺在垫子上蒸馒头蒸窝头,蒸出来不易黏皮,而且味道香甜可口。
各家的全体成员早早吃过晚饭,拿着板凳马扎,三五成群,像是过节一样,走进场院里。他们坐在玉米堆里,撕掉玉米外面的硬皮,露出如蚱蜢内翅般的内皮,再将多数内皮撕掉,只留一两张,卷实,将两只剥好的玉米相对打个结,再将另一只剥好的玉米编上去。如此,一只一只地相接,像辫子一样编在一起,直到编成一条长龙,将黄澄澄的长龙搭在墙头或是挂在木桩上,便于晾晒。
夕阳斜照,场院里,大家都在大声说笑着。既为丰收欢喜,也为这些玉米皮兴奋。忙碌之间,夜幕展开,场院里亮起灯,人们都隐藏在一座座小山似的玉米堆里,双手在白色的皮衣上跳动。大家都在抓住这一年一次的机会,争取多挣一些玉米皮回家。
场院也是孩子们的天堂。他们玩闹着,在小山之间窜来窜去,追逐打闹捉迷藏。有的就地取材,撕一把黑色的玉米须,咬在嘴里,扮作京戏里的张飞刘备。有的将玉米秆去掉叶子,做成金箍棒,相互招架击打。有的在玉米秆前端插上两根小棍,当做机枪,嘴里还嘟嘟着,像在射出子弹。玩闹够了,孩子们也会干活。他们不会编玉米,却会把那些小的不能入编的玉米直接剥掉外皮扔在大堆里。
夜色深了,月亮升到半空。场院里安静下来,蟋蟀的叫声此起彼伏,雾气开始弥漫,绿色的小山慢慢地变矮消失,成为一个个闪闪发黄的丘陵。人们在薄薄的雾气里浮现,一条条黄澄澄的长龙在脚下蜿蜒开来。
我又累又困,人影和虫声似乎远去了,却又觉得身体在晃动,像是躺在摇摆的秋千上。我睁开眼睛,发现那轮明月正挂在头顶上,向我微微地轻笑。原来,我睡在了独轮小车上,父亲正推着我往家走。车上堆满了绵软的玉米皮,母亲、姐姐一起在后面走着,疲惫而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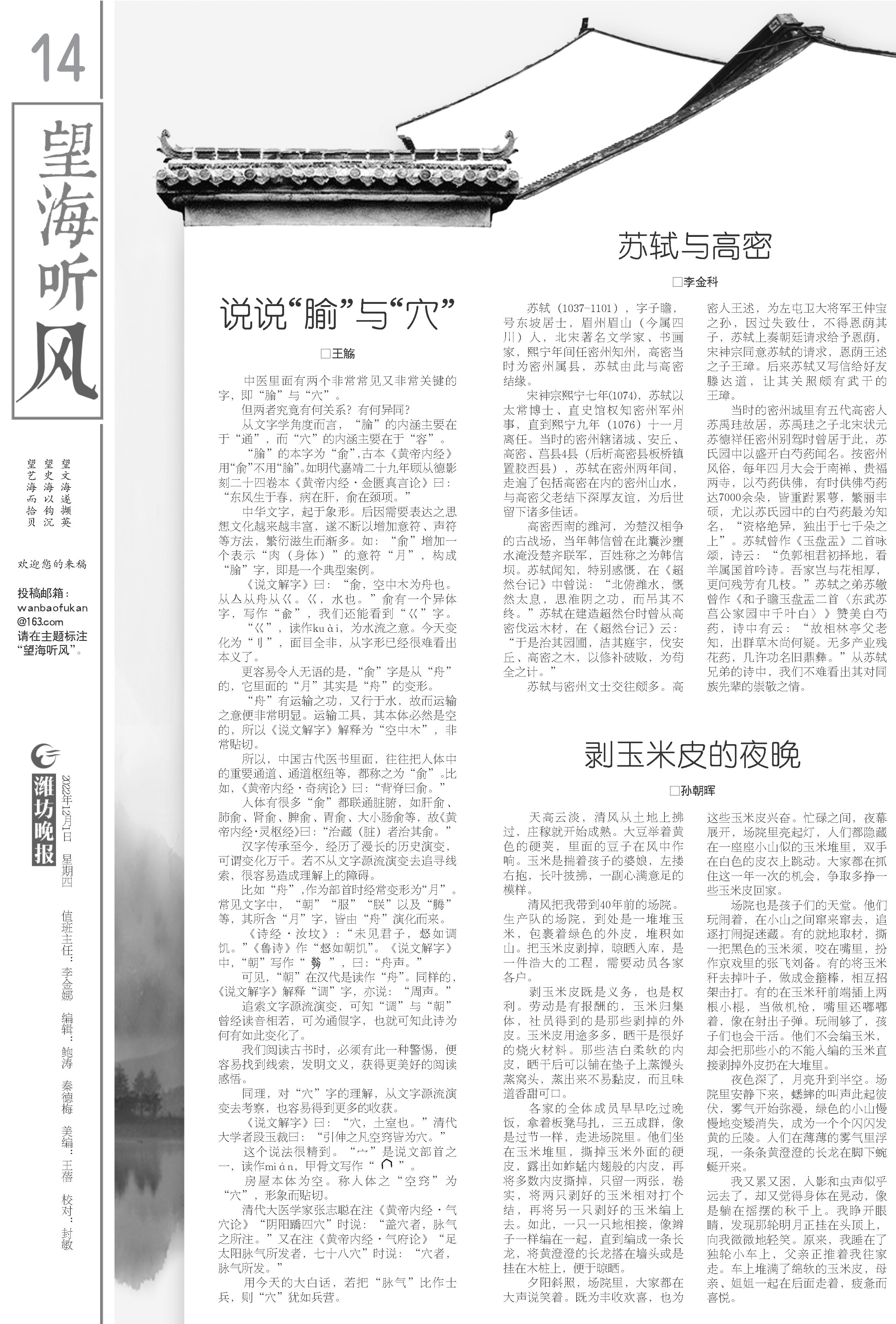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09/Page09-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15/Page15-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21201/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