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尼山对话
数字之约
 06版:风筝之爱
06版:风筝之爱
- *
高考后无偿献血
以热血铭记青春 - * 女子落水生命垂危 四位好汉齐心救人
- * 助老“一对一”
- * 守护“夕阳红”
- * 给老人送“福”
 15版:光影记录
15版:光影记录
- * 夏日雨荷
□李清云
回家,多么温暖的一个词语,像母亲的呼唤,只有远离家的人才能听见。
“到哪儿了?”母亲一遍又一遍打来电话。早晨八点从青州出发回高密,午后一点了,我和爱人还在安丘的地界上,车子正陷在雨后的泥坑里一时出不来。这是2009年我回娘家路上的一次经历,那是我到青州的第十个年头。
我老家在高密市西南,距离高密城区约30公里,与诸城市、安丘市搭界。刚到青州那年,我在邵庄镇山区工作,回娘家时要早早到村头等汽车,坐着汽车去火车站。等到绿皮火车终于“咣当咣当”地来了,大家必须跑着、挤着,蜂拥而上。绿皮车速度慢,停靠次数多,每次都要花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高密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去坐汽车,汽车出了站要在高密城里转悠半天,直到车里人满为患才出发。等到下了汽车,距离我家还有两三里路。每每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开始张罗这一天的晚饭了。
为避开这种消耗,我会选择长途汽车。有一趟大客车从淄博出发,途经青州、安丘、高密,经过我们村所在的乡镇。可是问题又来了,客车随时上下人,走走停停,我晕车晕得厉害。后来有了儿子,他也晕车,小脸蜡黄,叫人心疼。经过三个县市交界路段,坑多、洼多,车子左摇右晃,弄得晕车的人像生了一场难熬的病,于是我常常下定决心,再也不坐长途汽车。可是下次再坐火车兜兜转转精疲力尽时,又下定决心再也不坐火车了。回家的路,总是很长很长!
回家,多么潮湿的一个词语,每每被思念打湿了心扉,每每又有苦恼相伴相随。
2009年,我们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第一辆私家车,从此再也不用为坐长途汽车或坐火车纠结了,从此我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地栖落在故乡的枝头。可是私家车没有翅膀,路上层出不穷的状况还是给我们带来了烦恼。这一年的暑假,我们第一次开车回高密。前天夜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经过安丘市时遇上一段省道正在维修,我们便绕进了一条村道,道路两边是大片玉米青纱帐,路面坑洼不平,越来越难走,结果陷在一个泥坑里,车轮原地打转,车子纹丝不动。
“到哪儿了?”母亲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大夏天的,大中午的,漫漫青纱帐,路上没有一个行人。爱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埋怨这该死的道路。突然间他生出一个主意,让我去弄些玉米秸秆。我虽觉得不妥,可是看看眼前这情况,想想母亲的担忧,也只好去了。我弄来玉米秸秆垫在车前轮处,爱人发动车子猛踩油门,果然起了作用。就在我们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玉米地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扛着铁锹,大声喊道:“你们是哪里人,怎么能糟蹋我家的庄稼呢?不赔钱就别想走!”虽是不得已,可折了人家的庄稼是真的。那人拿着铁锹喊叫着,把我爱人刚刚平复的情绪又给激怒了,他俩互不相让。我赶紧劝说,好说歹说,给了那人十几块钱,他总算离开了。
“到哪儿了?”母亲的电话最后一次打来时已是午后一点半了,我们饥肠辘辘,父母牵肠挂肚。数一数有多少回家的日子,就有多少难忘的经历,那些纵横交错的道路,编织成密密麻麻的记忆,刻在我颠簸的、辛苦的、难忘的、期盼的回家之路上。
困难的日子总是难捱,幸福的时光总是匆匆。从买回第一辆私家车到拥有第二辆私家车,转眼又是十年,忽然间意识到,近几年走省道路过三县交界时的那些坑坑洼洼消失了。多少年来,每每经过,每每牢骚,既盼着快些到这儿,又怕经过这儿,这儿早已成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不知不觉中,省道平坦了、宽阔了,多条高速公路通车了。如果出发得早,我们就走省道回家,沿途吃早餐,下车看风景;要是出发得晚,我们就会在高速上行驶一段,快捷又安全,觉得高速不再那么遥远,不再让人望而生畏。
不知不觉中,D字头、T字头、K字头的火车经过青州市、高密市小站,穿行、停靠,那么漂亮、那么安静,我再也不用眼巴巴地望着时间走得那么缓慢,再也不用跑着去抢座,再也不用挤着上火车。
回家路上,省道破损的路面少了,维修的路障少了;高速路在节假日里免费了;三县交界的“三不管”地带一马平川了;村前的那道沟坎不知何时填平了,我们竟然只用两个多小时就能到家了。时光荏苒,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我这个普通人用二十年的回家之路见证了身边交通条件的改善。村庄、城镇、高楼、旷野、绿树、阳光,一切的一切正从车窗外飞过,我的心中四通八达。
回家,多么温暖的一个词语,像母亲的呼唤,只有远离家的人才能听见。
“到哪儿了?”母亲一遍又一遍打来电话。早晨八点从青州出发回高密,午后一点了,我和爱人还在安丘的地界上,车子正陷在雨后的泥坑里一时出不来。这是2009年我回娘家路上的一次经历,那是我到青州的第十个年头。
我老家在高密市西南,距离高密城区约30公里,与诸城市、安丘市搭界。刚到青州那年,我在邵庄镇山区工作,回娘家时要早早到村头等汽车,坐着汽车去火车站。等到绿皮火车终于“咣当咣当”地来了,大家必须跑着、挤着,蜂拥而上。绿皮车速度慢,停靠次数多,每次都要花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高密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去坐汽车,汽车出了站要在高密城里转悠半天,直到车里人满为患才出发。等到下了汽车,距离我家还有两三里路。每每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开始张罗这一天的晚饭了。
为避开这种消耗,我会选择长途汽车。有一趟大客车从淄博出发,途经青州、安丘、高密,经过我们村所在的乡镇。可是问题又来了,客车随时上下人,走走停停,我晕车晕得厉害。后来有了儿子,他也晕车,小脸蜡黄,叫人心疼。经过三个县市交界路段,坑多、洼多,车子左摇右晃,弄得晕车的人像生了一场难熬的病,于是我常常下定决心,再也不坐长途汽车。可是下次再坐火车兜兜转转精疲力尽时,又下定决心再也不坐火车了。回家的路,总是很长很长!
回家,多么潮湿的一个词语,每每被思念打湿了心扉,每每又有苦恼相伴相随。
2009年,我们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第一辆私家车,从此再也不用为坐长途汽车或坐火车纠结了,从此我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地栖落在故乡的枝头。可是私家车没有翅膀,路上层出不穷的状况还是给我们带来了烦恼。这一年的暑假,我们第一次开车回高密。前天夜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经过安丘市时遇上一段省道正在维修,我们便绕进了一条村道,道路两边是大片玉米青纱帐,路面坑洼不平,越来越难走,结果陷在一个泥坑里,车轮原地打转,车子纹丝不动。
“到哪儿了?”母亲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大夏天的,大中午的,漫漫青纱帐,路上没有一个行人。爱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埋怨这该死的道路。突然间他生出一个主意,让我去弄些玉米秸秆。我虽觉得不妥,可是看看眼前这情况,想想母亲的担忧,也只好去了。我弄来玉米秸秆垫在车前轮处,爱人发动车子猛踩油门,果然起了作用。就在我们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玉米地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扛着铁锹,大声喊道:“你们是哪里人,怎么能糟蹋我家的庄稼呢?不赔钱就别想走!”虽是不得已,可折了人家的庄稼是真的。那人拿着铁锹喊叫着,把我爱人刚刚平复的情绪又给激怒了,他俩互不相让。我赶紧劝说,好说歹说,给了那人十几块钱,他总算离开了。
“到哪儿了?”母亲的电话最后一次打来时已是午后一点半了,我们饥肠辘辘,父母牵肠挂肚。数一数有多少回家的日子,就有多少难忘的经历,那些纵横交错的道路,编织成密密麻麻的记忆,刻在我颠簸的、辛苦的、难忘的、期盼的回家之路上。
困难的日子总是难捱,幸福的时光总是匆匆。从买回第一辆私家车到拥有第二辆私家车,转眼又是十年,忽然间意识到,近几年走省道路过三县交界时的那些坑坑洼洼消失了。多少年来,每每经过,每每牢骚,既盼着快些到这儿,又怕经过这儿,这儿早已成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不知不觉中,省道平坦了、宽阔了,多条高速公路通车了。如果出发得早,我们就走省道回家,沿途吃早餐,下车看风景;要是出发得晚,我们就会在高速上行驶一段,快捷又安全,觉得高速不再那么遥远,不再让人望而生畏。
不知不觉中,D字头、T字头、K字头的火车经过青州市、高密市小站,穿行、停靠,那么漂亮、那么安静,我再也不用眼巴巴地望着时间走得那么缓慢,再也不用跑着去抢座,再也不用挤着上火车。
回家路上,省道破损的路面少了,维修的路障少了;高速路在节假日里免费了;三县交界的“三不管”地带一马平川了;村前的那道沟坎不知何时填平了,我们竟然只用两个多小时就能到家了。时光荏苒,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我这个普通人用二十年的回家之路见证了身边交通条件的改善。村庄、城镇、高楼、旷野、绿树、阳光,一切的一切正从车窗外飞过,我的心中四通八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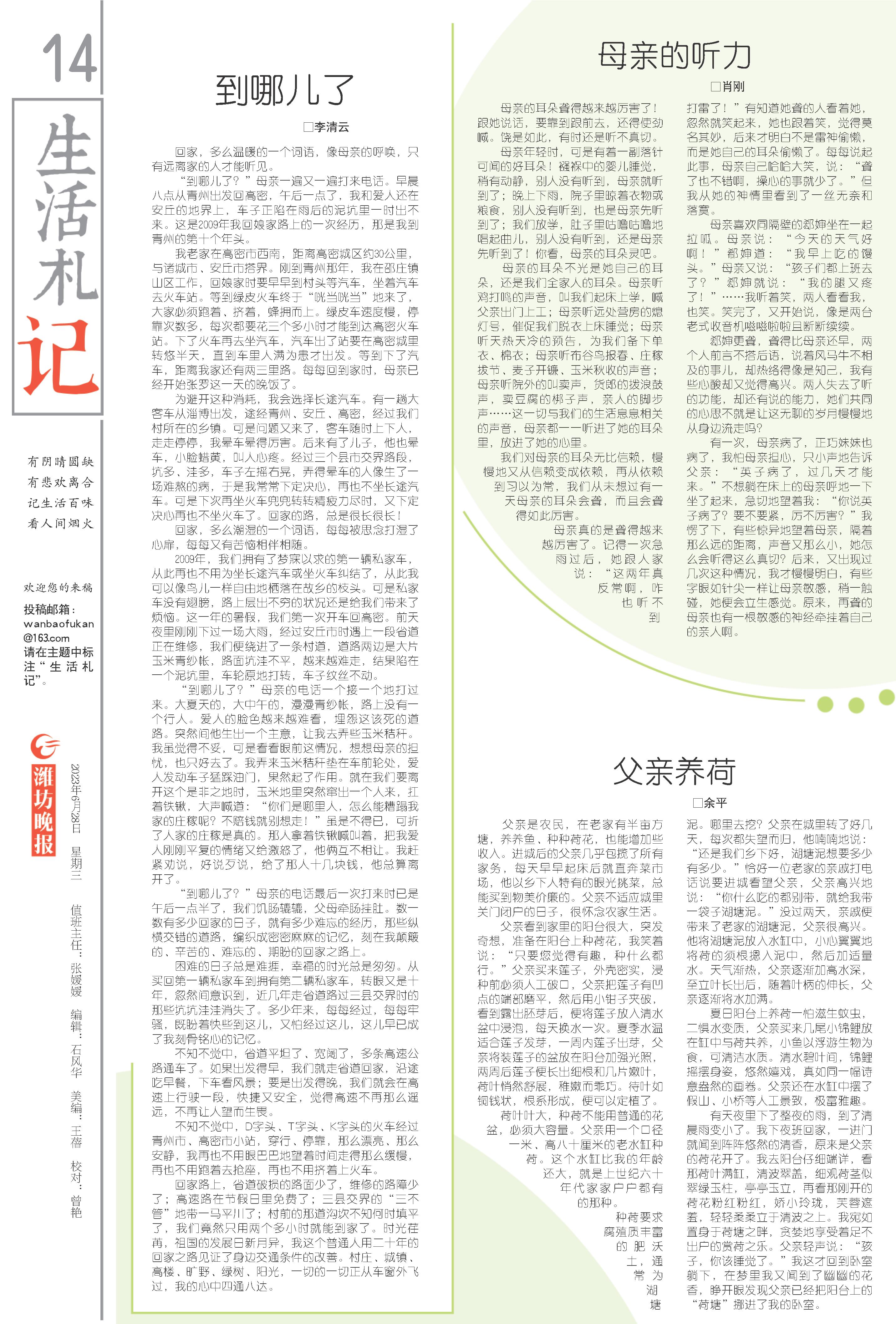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15/Page15-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28/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