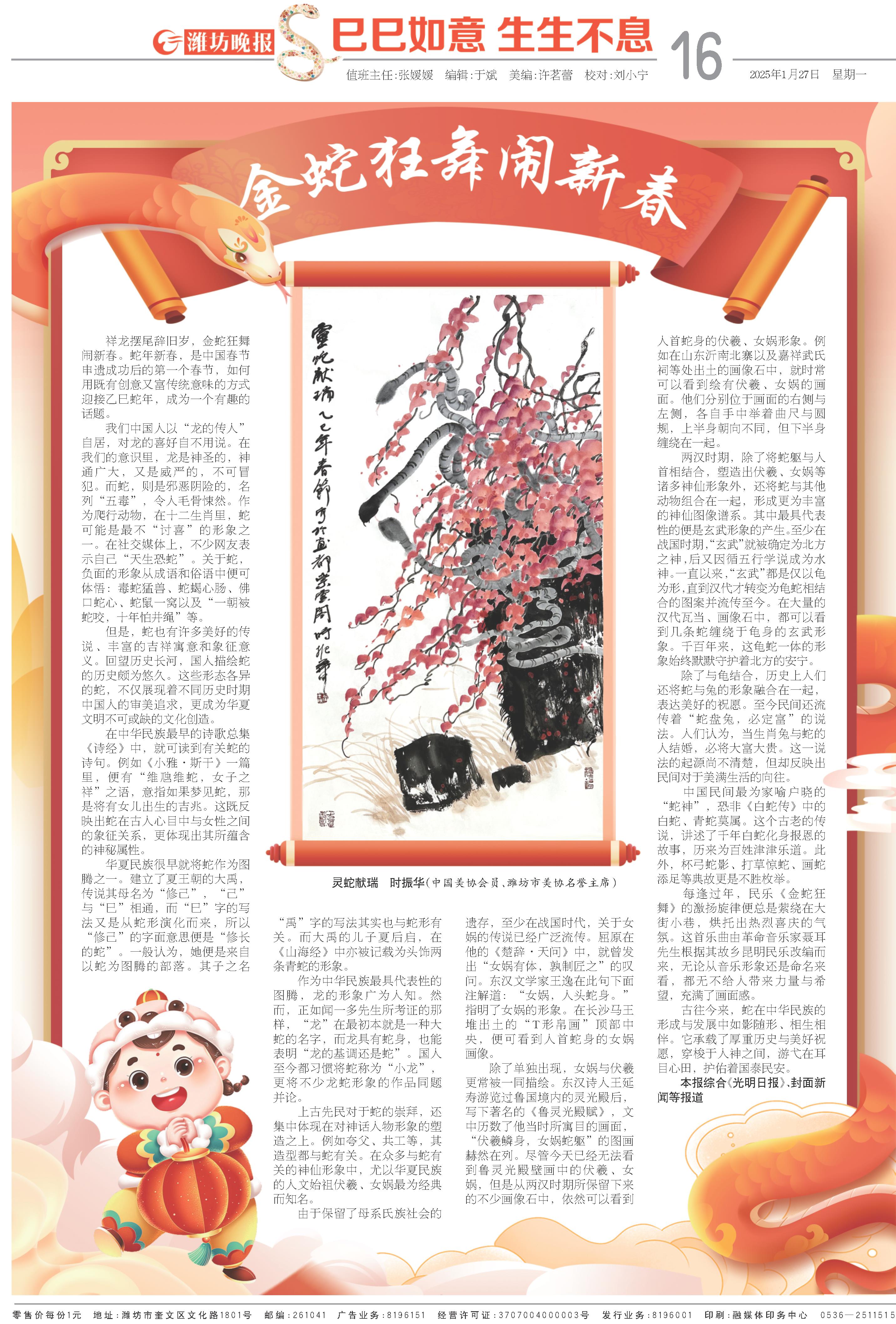01版:春节版
01版:春节版
- *
巳巳如意
生生不息
 10版:巳巳如意 生生不息
10版:巳巳如意 生生不息
- * 带动更多人走上技能成才之路
- * 用坚持和付出赢得荣誉
- * 为中国动力追梦前行
 11版:巳巳如意 生生不息
11版:巳巳如意 生生不息
- * 愿为更多人带去健康与希望
- * 把好音乐分享给更多人
- * 做一个发光发热的人
 15版:巳巳如意 生生不息
15版:巳巳如意 生生不息
- * 那抹温馨的年味
- * 重拾年韵
- *
此生漫长的路
是回家的路
 16版:巳巳如意 生生不息
16版:巳巳如意 生生不息
- * 金蛇狂舞闹新春
祥龙摆尾辞旧岁,金蛇狂舞闹新春。蛇年新春,是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如何用既有创意又富传统意味的方式迎接乙巳蛇年,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自居,对龙的喜好自不用说。在我们的意识里,龙是神圣的,神通广大,又是威严的,不可冒犯。而蛇,则是邪恶阴险的,名列“五毒”,令人毛骨悚然。作为爬行动物,在十二生肖里,蛇可能是最不“讨喜”的形象之一。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天生恐蛇”。关于蛇,负面的形象从成语和俗语中便可体悟:毒蛇猛兽、蛇蝎心肠、佛口蛇心、蛇鼠一窝以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等。
但是,蛇也有许多美好的传说、丰富的吉祥寓意和象征意义。回望历史长河,国人描绘蛇的历史颇为悠久。这些形态各异的蛇,不仅展现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更成为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创造。
在中华民族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可读到有关蛇的诗句。例如《小雅·斯干》一篇里,便有“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之语,意指如果梦见蛇,那是将有女儿出生的吉兆。这既反映出蛇在古人心目中与女性之间的象征关系,更体现出其所蕴含的神秘属性。
华夏民族很早就将蛇作为图腾之一。建立了夏王朝的大禹,传说其母名为“修己”,“己”与“巳”相通,而“巳”字的写法又是从蛇形演化而来,所以“修己”的字面意思便是“修长的蛇”。一般认为,她便是来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其子之名“禹”字的写法其实也与蛇形有关。而大禹的儿子夏后启,在《山海经》中亦被记载为头饰两条青蛇的形象。
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图腾,龙的形象广为人知。然而,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考证的那样,“龙”在最初本就是一种大蛇的名字,而龙具有蛇身,也能表明“龙的基调还是蛇”。国人至今都习惯将蛇称为“小龙”,更将不少龙蛇形象的作品同题并论。
上古先民对于蛇的崇拜,还集中体现在对神话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例如夸父、共工等,其造型都与蛇有关。在众多与蛇有关的神仙形象中,尤以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最为经典而知名。
由于保留了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至少在战国时代,关于女娲的传说已经广泛流传。屈原在他的《楚辞·天问》中,就曾发出“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的叹问。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此句下面注解道:“女娲,人头蛇身。”指明了女娲的形象。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T形帛画”顶部中央,便可看到人首蛇身的女娲画像。
除了单独出现,女娲与伏羲更常被一同描绘。东汉诗人王延寿游览过鲁国境内的灵光殿后,写下著名的《鲁灵光殿赋》,文中历数了他当时所寓目的画面,“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图画赫然在列。尽管今天已经无法看到鲁灵光殿壁画中的伏羲、女娲,但是从两汉时期所保留下来的不少画像石中,依然可以看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例如在山东沂南北寨以及嘉祥武氏祠等处出土的画像石中,就时常可以看到绘有伏羲、女娲的画面。他们分别位于画面的右侧与左侧,各自手中举着曲尺与圆规,上半身朝向不同,但下半身缠绕在一起。
两汉时期,除了将蛇躯与人首相结合,塑造出伏羲、女娲等诸多神仙形象外,还将蛇与其他动物组合在一起,形成更为丰富的神仙图像谱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玄武形象的产生。至少在战国时期,“玄武”就被确定为北方之神,后又因循五行学说成为水神。一直以来,“玄武”都是仅以龟为形,直到汉代才转变为龟蛇相结合的图案并流传至今。在大量的汉代瓦当、画像石中,都可以看到几条蛇缠绕于龟身的玄武形象。千百年来,这龟蛇一体的形象始终默默守护着北方的安宁。
除了与龟结合,历史上人们还将蛇与兔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表达美好的祝愿。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蛇盘兔,必定富”的说法。人们认为,当生肖兔与蛇的人结婚,必将大富大贵。这一说法的起源尚不清楚,但却反映出民间对于美满生活的向往。
中国民间最为家喻户晓的“蛇神”,恐非《白蛇传》中的白蛇、青蛇莫属。这个古老的传说,讲述了千年白蛇化身报恩的故事,历来为百姓津津乐道。此外,杯弓蛇影、打草惊蛇、画蛇添足等典故更是不胜枚举。
每逢过年,民乐《金蛇狂舞》的激扬旋律便总是萦绕在大街小巷,烘托出热烈喜庆的气氛。这首乐曲由革命音乐家聂耳先生根据其故乡昆明民乐改编而来,无论从音乐形象还是命名来看,都无不给人带来力量与希望,充满了画面感。
古往今来,蛇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如影随形、相生相伴。它承载了厚重历史与美好祝愿,穿梭于人神之间,游弋在耳目心田,护佑着国泰民安。
本报综合《光明日报》、封面新闻等报道
我们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自居,对龙的喜好自不用说。在我们的意识里,龙是神圣的,神通广大,又是威严的,不可冒犯。而蛇,则是邪恶阴险的,名列“五毒”,令人毛骨悚然。作为爬行动物,在十二生肖里,蛇可能是最不“讨喜”的形象之一。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天生恐蛇”。关于蛇,负面的形象从成语和俗语中便可体悟:毒蛇猛兽、蛇蝎心肠、佛口蛇心、蛇鼠一窝以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等。
但是,蛇也有许多美好的传说、丰富的吉祥寓意和象征意义。回望历史长河,国人描绘蛇的历史颇为悠久。这些形态各异的蛇,不仅展现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更成为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创造。
在中华民族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可读到有关蛇的诗句。例如《小雅·斯干》一篇里,便有“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之语,意指如果梦见蛇,那是将有女儿出生的吉兆。这既反映出蛇在古人心目中与女性之间的象征关系,更体现出其所蕴含的神秘属性。
华夏民族很早就将蛇作为图腾之一。建立了夏王朝的大禹,传说其母名为“修己”,“己”与“巳”相通,而“巳”字的写法又是从蛇形演化而来,所以“修己”的字面意思便是“修长的蛇”。一般认为,她便是来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其子之名“禹”字的写法其实也与蛇形有关。而大禹的儿子夏后启,在《山海经》中亦被记载为头饰两条青蛇的形象。
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图腾,龙的形象广为人知。然而,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考证的那样,“龙”在最初本就是一种大蛇的名字,而龙具有蛇身,也能表明“龙的基调还是蛇”。国人至今都习惯将蛇称为“小龙”,更将不少龙蛇形象的作品同题并论。
上古先民对于蛇的崇拜,还集中体现在对神话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例如夸父、共工等,其造型都与蛇有关。在众多与蛇有关的神仙形象中,尤以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最为经典而知名。
由于保留了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至少在战国时代,关于女娲的传说已经广泛流传。屈原在他的《楚辞·天问》中,就曾发出“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的叹问。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此句下面注解道:“女娲,人头蛇身。”指明了女娲的形象。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T形帛画”顶部中央,便可看到人首蛇身的女娲画像。
除了单独出现,女娲与伏羲更常被一同描绘。东汉诗人王延寿游览过鲁国境内的灵光殿后,写下著名的《鲁灵光殿赋》,文中历数了他当时所寓目的画面,“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图画赫然在列。尽管今天已经无法看到鲁灵光殿壁画中的伏羲、女娲,但是从两汉时期所保留下来的不少画像石中,依然可以看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例如在山东沂南北寨以及嘉祥武氏祠等处出土的画像石中,就时常可以看到绘有伏羲、女娲的画面。他们分别位于画面的右侧与左侧,各自手中举着曲尺与圆规,上半身朝向不同,但下半身缠绕在一起。
两汉时期,除了将蛇躯与人首相结合,塑造出伏羲、女娲等诸多神仙形象外,还将蛇与其他动物组合在一起,形成更为丰富的神仙图像谱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玄武形象的产生。至少在战国时期,“玄武”就被确定为北方之神,后又因循五行学说成为水神。一直以来,“玄武”都是仅以龟为形,直到汉代才转变为龟蛇相结合的图案并流传至今。在大量的汉代瓦当、画像石中,都可以看到几条蛇缠绕于龟身的玄武形象。千百年来,这龟蛇一体的形象始终默默守护着北方的安宁。
除了与龟结合,历史上人们还将蛇与兔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表达美好的祝愿。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蛇盘兔,必定富”的说法。人们认为,当生肖兔与蛇的人结婚,必将大富大贵。这一说法的起源尚不清楚,但却反映出民间对于美满生活的向往。
中国民间最为家喻户晓的“蛇神”,恐非《白蛇传》中的白蛇、青蛇莫属。这个古老的传说,讲述了千年白蛇化身报恩的故事,历来为百姓津津乐道。此外,杯弓蛇影、打草惊蛇、画蛇添足等典故更是不胜枚举。
每逢过年,民乐《金蛇狂舞》的激扬旋律便总是萦绕在大街小巷,烘托出热烈喜庆的气氛。这首乐曲由革命音乐家聂耳先生根据其故乡昆明民乐改编而来,无论从音乐形象还是命名来看,都无不给人带来力量与希望,充满了画面感。
古往今来,蛇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如影随形、相生相伴。它承载了厚重历史与美好祝愿,穿梭于人神之间,游弋在耳目心田,护佑着国泰民安。
本报综合《光明日报》、封面新闻等报道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127/16/16-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