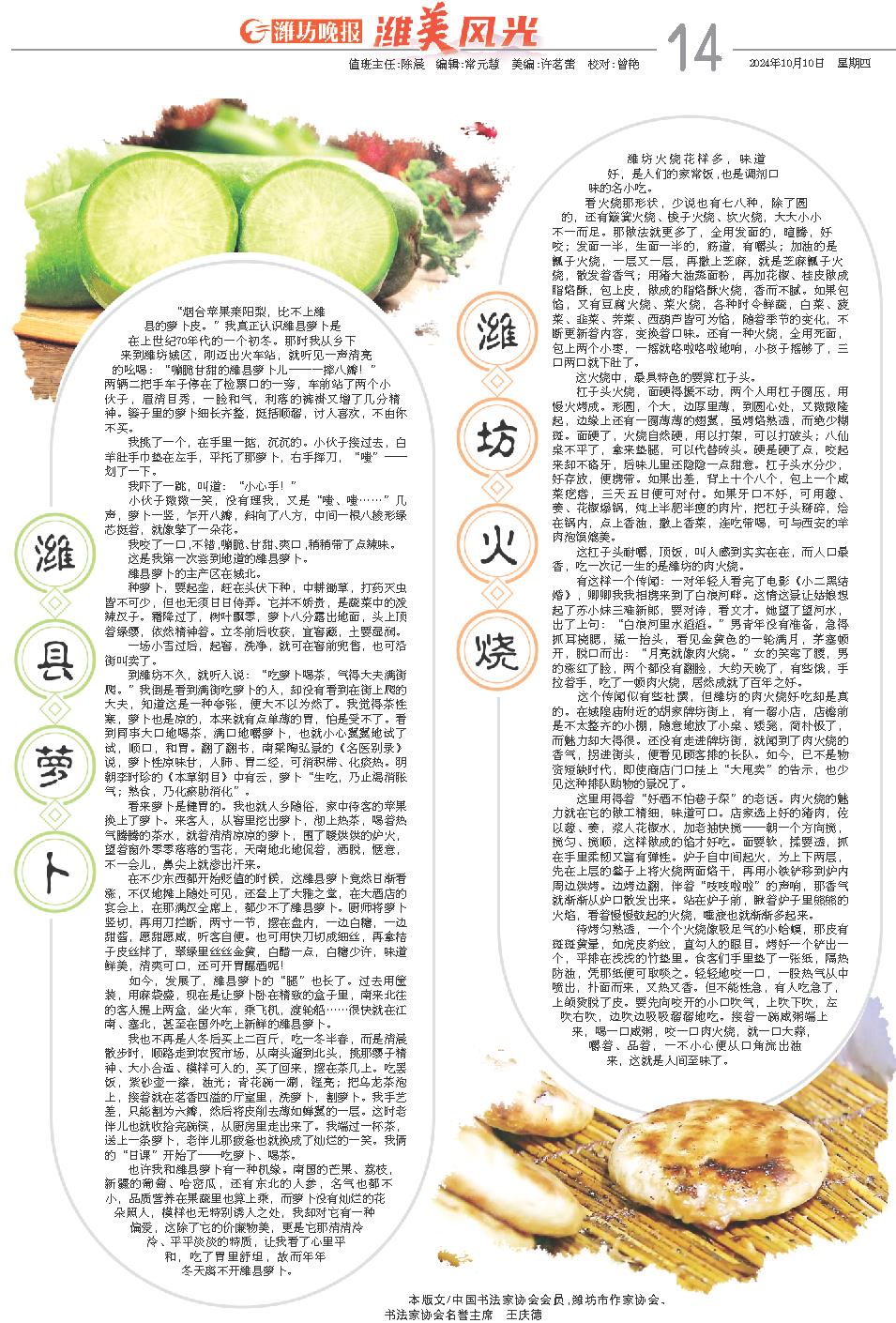05版:社会新闻
05版:社会新闻
- * 小山村编出高质量村志
- *
世界风筝公园
邀请老人免费赏菊 - * 126份蔬菜礼包送老人
- * 多彩活动庆重阳
- * 情暖老兵送慰问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城市是一首RAP
“烟台苹果莱阳梨,比不上潍县的萝卜皮。”我真正认识潍县萝卜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初冬。那时我从乡下来到潍坊城区,刚迈出火车站,就听见一声清亮的吆喝:“嘣脆甘甜的潍县萝卜儿——一摔八瓣!”两辆二把手车子停在了检票口的一旁,车前站了两个小伙子,眉清目秀,一脸和气,利落的裤褂又增了几分精神。篓子里的萝卜细长齐整,挺括顺溜,讨人喜欢,不由你不买。
我挑了一个,在手里一掂,沉沉的。小伙子接过去,白羊肚手巾垫在左手,平托了那萝卜,右手挥刀,“嗤”——划了一下。
我吓了一跳,叫道:“小心手!”
小伙子微微一笑,没有理我,又是“嗤、嗤……”几声,萝卜一竖,乍开八瓣,斜向了八方,中间一根八棱形绿芯挺着,就像擎了一朵花。
我咬了一口,不错,嘣脆、甘甜、爽口,稍稍带了点辣味。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地道的潍县萝卜。
潍县萝卜的主产区在城北。
种萝卜,要起垄,赶在头伏下种,中耕锄草,打药灭虫皆不可少,但也无须日日侍弄。它并不娇贵,是蔬菜中的泼辣汉子。霜降过了,树叶飘零,萝卜八分露出地面,头上顶着绿缨,依然精神着。立冬前后收获,宜窖藏,土要湿润。
一场小雪过后,起窖,洗净,就可在窖前兜售,也可沿街叫卖了。
到潍坊不久,就听人说:“吃萝卜喝茶,气得大夫满街爬。”我倒是看到满街吃萝卜的人,却没有看到在街上爬的大夫,知道这是一种夸张,便大不以为然了。我觉得茶性寒,萝卜也是凉的,本来就有点单薄的胃,怕是受不了。看到同事大口地喝茶,满口地嚼萝卜,也就小心翼翼地试了试,顺口,和胃。翻了翻书,南梁陶弘景的《名医别录》说,萝卜性凉味甘,入肺、胃二经,可消积滞、化痰热。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云,萝卜“生吃,乃止渴消胀气;熟食,乃化瘀助消化”。
看来萝卜是健胃的。我也就入乡随俗,家中待客的苹果换上了萝卜。来客人,从窖里挖出萝卜,沏上热茶,喝着热气腾腾的茶水,就着清清凉凉的萝卜,围了暖烘烘的炉火,望着窗外零零落落的雪花,天南地北地侃着,洒脱,惬意,不一会儿,鼻尖上就渗出汗来。
在不少东西都开始贬值的时候,这潍县萝卜竟然日渐看涨,不仅地摊上随处可见,还登上了大雅之堂,在大酒店的宴会上,在那满汉全席上,都少不了潍县萝卜。厨师将萝卜竖切,再用刀拦断,两寸一节,摆在盘内,一边白糖,一边甜酱,愿甜愿咸,听客自便。也可用快刀切成细丝,再拿桔子皮丝拌了,翠绿里丝丝金黄,白醋一点,白糖少许,味道鲜美,清爽可口,还可开胃醒酒呢!
如今,发展了,潍县萝卜的“腿”也长了。过去用筐装,用麻袋盛,现在是让萝卜卧在精致的盒子里,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上两盒,坐火车,乘飞机,渡轮船……很快就在江南、塞北,甚至在国外吃上新鲜的潍县萝卜。
我也不再是入冬后买上二百斤,吃一冬半春,而是清晨散步时,顺路走到农贸市场,从南头遛到北头,挑那缨子精神、大小合适、模样可人的,买了回来,摆在茶几上。吃罢饭,紫砂壶一擦,油光;青花碗一涮,锃亮;把乌龙茶泡上,接着就在茗香四溢的厅室里,洗萝卜,割萝卜。我手艺差,只能割为六瓣,然后将皮削去薄如蝉翼的一层。这时老伴儿也就收拾完碗筷,从厨房里走出来了。我端过一杯茶,送上一条萝卜,老伴儿那疲惫也就换成了灿烂的一笑。我俩的“日课”开始了——吃萝卜、喝茶。
也许我和潍县萝卜有一种机缘。南国的芒果、荔枝,新疆的葡萄、哈密瓜,还有东北的人参,名气也都不小,品质营养在果蔬里也算上乘,而萝卜没有灿烂的花朵照人,模样也无特别诱人之处,我却对它有一种偏爱,这除了它的价廉物美,更是它那清清泠泠、平平淡淡的特质,让我看了心里平和,吃了胃里舒坦,故而年年冬天离不开潍县萝卜。
我挑了一个,在手里一掂,沉沉的。小伙子接过去,白羊肚手巾垫在左手,平托了那萝卜,右手挥刀,“嗤”——划了一下。
我吓了一跳,叫道:“小心手!”
小伙子微微一笑,没有理我,又是“嗤、嗤……”几声,萝卜一竖,乍开八瓣,斜向了八方,中间一根八棱形绿芯挺着,就像擎了一朵花。
我咬了一口,不错,嘣脆、甘甜、爽口,稍稍带了点辣味。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地道的潍县萝卜。
潍县萝卜的主产区在城北。
种萝卜,要起垄,赶在头伏下种,中耕锄草,打药灭虫皆不可少,但也无须日日侍弄。它并不娇贵,是蔬菜中的泼辣汉子。霜降过了,树叶飘零,萝卜八分露出地面,头上顶着绿缨,依然精神着。立冬前后收获,宜窖藏,土要湿润。
一场小雪过后,起窖,洗净,就可在窖前兜售,也可沿街叫卖了。
到潍坊不久,就听人说:“吃萝卜喝茶,气得大夫满街爬。”我倒是看到满街吃萝卜的人,却没有看到在街上爬的大夫,知道这是一种夸张,便大不以为然了。我觉得茶性寒,萝卜也是凉的,本来就有点单薄的胃,怕是受不了。看到同事大口地喝茶,满口地嚼萝卜,也就小心翼翼地试了试,顺口,和胃。翻了翻书,南梁陶弘景的《名医别录》说,萝卜性凉味甘,入肺、胃二经,可消积滞、化痰热。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云,萝卜“生吃,乃止渴消胀气;熟食,乃化瘀助消化”。
看来萝卜是健胃的。我也就入乡随俗,家中待客的苹果换上了萝卜。来客人,从窖里挖出萝卜,沏上热茶,喝着热气腾腾的茶水,就着清清凉凉的萝卜,围了暖烘烘的炉火,望着窗外零零落落的雪花,天南地北地侃着,洒脱,惬意,不一会儿,鼻尖上就渗出汗来。
在不少东西都开始贬值的时候,这潍县萝卜竟然日渐看涨,不仅地摊上随处可见,还登上了大雅之堂,在大酒店的宴会上,在那满汉全席上,都少不了潍县萝卜。厨师将萝卜竖切,再用刀拦断,两寸一节,摆在盘内,一边白糖,一边甜酱,愿甜愿咸,听客自便。也可用快刀切成细丝,再拿桔子皮丝拌了,翠绿里丝丝金黄,白醋一点,白糖少许,味道鲜美,清爽可口,还可开胃醒酒呢!
如今,发展了,潍县萝卜的“腿”也长了。过去用筐装,用麻袋盛,现在是让萝卜卧在精致的盒子里,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上两盒,坐火车,乘飞机,渡轮船……很快就在江南、塞北,甚至在国外吃上新鲜的潍县萝卜。
我也不再是入冬后买上二百斤,吃一冬半春,而是清晨散步时,顺路走到农贸市场,从南头遛到北头,挑那缨子精神、大小合适、模样可人的,买了回来,摆在茶几上。吃罢饭,紫砂壶一擦,油光;青花碗一涮,锃亮;把乌龙茶泡上,接着就在茗香四溢的厅室里,洗萝卜,割萝卜。我手艺差,只能割为六瓣,然后将皮削去薄如蝉翼的一层。这时老伴儿也就收拾完碗筷,从厨房里走出来了。我端过一杯茶,送上一条萝卜,老伴儿那疲惫也就换成了灿烂的一笑。我俩的“日课”开始了——吃萝卜、喝茶。
也许我和潍县萝卜有一种机缘。南国的芒果、荔枝,新疆的葡萄、哈密瓜,还有东北的人参,名气也都不小,品质营养在果蔬里也算上乘,而萝卜没有灿烂的花朵照人,模样也无特别诱人之处,我却对它有一种偏爱,这除了它的价廉物美,更是它那清清泠泠、平平淡淡的特质,让我看了心里平和,吃了胃里舒坦,故而年年冬天离不开潍县萝卜。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08 09/08 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15/Page15-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1010/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