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夏夜邀约
品味美好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夜游沂山 一起吗
□高玉宝
砚台,大家都熟知四大名砚,少知著名的红丝砚。产于山东青州黑山的红丝砚盛行于唐宋,柳公权等人对其盛赞有加,一度排名在端砚、歙砚之前。红丝砚贮墨经久不干,用过以后,用水一洗,光洁如新。后来,因为青州红丝矿枯竭,此砚渐渐不为后人所知。如今开采技术进步,人们在青州附近的临朐等地再次发现了红丝石,制砚简单,磨平即成砚。如有雅趣及雕艺,可在砚台上雕上诗词雅句,亦可描梅画竹。龙凤太俗,一般不会雕于砚上。
清代书画家高凤翰对红丝砚十分钟爱,尽管他是安徽歙县县丞,歙砚易取,但并不影响他喜好收藏红丝砚并在砚上刻有“芙蓉井”诗句。高凤翰老家胶州,离青州很近,也许是他喜好红丝砚的一个原因。古人好玩,一方砚台也要弄出许多花样,研墨还要找一个红袖佳人立于书生身旁,满目深情。男人,转转手腕子、动动手都不能了?有佳人立于身旁,写字著述不受影响吗?或许古人定力了得,我辈不及。
砚台分石砚与陶砚,澄泥砚即是陶砚的代表。澄泥砚之泥取于汾水,那是名砚之泥,一般制砚人不得此泥,倒也有其他可替代的泥石。例如,在河道捡取泥质岩,松软、杂质少的泥质岩最佳。将泥石自河道背回,放入臼中捣成粉末,跟面粉差不多,或黄或红的泥石粉即成。山里无风,白云飘过,鸟鸣阵阵,制砚人脸上蒙着细汗,将杂质筛出,粉末放入缸中,木棍搅拌,让水转起来,转起缸中漩涡。缸中的泥水黏稠,散发着泥土的香气。慢慢沉淀,将水分沥出,只留河泥。用布裹起,放于筛下,好玩的工序来了——捶打河泥,一遍一遍,捶打九千九百九十九遍,将泥中空气挤出,直捶打得河泥像最细最细的面筋,摸起来像小孩子的屁股一样光滑,像爱人的肌肤一样绵软。河泥被制成长方体,用油纸裹严,放在阴凉房屋的木箱中,谓之,陈腐。
一年后打开油纸,河泥还是湿润的,散发着时间的味道。再次捶打、揉搓后,开始制胚。用木尺量好,用竹刀割开,放于阴凉处阴干。小孩子好玩泥巴,或许始于女娲补天的基因。如今带着化工味道的橡皮泥不好玩,少了泥土的亲近。
待泥胚接近干透之时,制砚人在灯下已经画好线稿,或画荷莲,或画鱼虫,也有画上人物的,骑于牛背上的牧童、放风筝的小孩,都挺好。将线稿贴在胚上,用刻刀雕胚。清晨,鸡叫声在山谷里传出很远,河水哗哗流淌,制砚人洗了脸,鸡窝里撒过米,扫过院子,用清水冲刷了门前的石板。朝阳已经从山的另一面射进道道红光,晨雾渐小。制砚人开始雕砚,一点一点,雪花一样的泥屑在刻刀下剥落,砚池慢慢显出轮廊。制砚人一遍一遍打磨,目光慈悲,满眼江河,如同看着眼前深爱的女人。
泥胚制好,放于柴炉,点火烧柴,窑口上的烟囱升起青烟。不停火,烧制两天左右,为受热均匀,用河泥将窑口封严,让木柴慢慢燃烧。十日后,开窑,这个急不得,急了,陶砚会开裂。拆开窑口,本来青白的泥胚变得橙红,敲打之下发出钢玉之声。
再一次精细打磨,从二百目砂条,一直磨到两千目。打磨也急不得,慢慢来,陶砚的光泽才会显现出来,玉影般沉静,美人眼眸一样温情如水。呵气则润,自带潮水。
一方古法所制陶砚成矣。
砚台,大家都熟知四大名砚,少知著名的红丝砚。产于山东青州黑山的红丝砚盛行于唐宋,柳公权等人对其盛赞有加,一度排名在端砚、歙砚之前。红丝砚贮墨经久不干,用过以后,用水一洗,光洁如新。后来,因为青州红丝矿枯竭,此砚渐渐不为后人所知。如今开采技术进步,人们在青州附近的临朐等地再次发现了红丝石,制砚简单,磨平即成砚。如有雅趣及雕艺,可在砚台上雕上诗词雅句,亦可描梅画竹。龙凤太俗,一般不会雕于砚上。
清代书画家高凤翰对红丝砚十分钟爱,尽管他是安徽歙县县丞,歙砚易取,但并不影响他喜好收藏红丝砚并在砚上刻有“芙蓉井”诗句。高凤翰老家胶州,离青州很近,也许是他喜好红丝砚的一个原因。古人好玩,一方砚台也要弄出许多花样,研墨还要找一个红袖佳人立于书生身旁,满目深情。男人,转转手腕子、动动手都不能了?有佳人立于身旁,写字著述不受影响吗?或许古人定力了得,我辈不及。
砚台分石砚与陶砚,澄泥砚即是陶砚的代表。澄泥砚之泥取于汾水,那是名砚之泥,一般制砚人不得此泥,倒也有其他可替代的泥石。例如,在河道捡取泥质岩,松软、杂质少的泥质岩最佳。将泥石自河道背回,放入臼中捣成粉末,跟面粉差不多,或黄或红的泥石粉即成。山里无风,白云飘过,鸟鸣阵阵,制砚人脸上蒙着细汗,将杂质筛出,粉末放入缸中,木棍搅拌,让水转起来,转起缸中漩涡。缸中的泥水黏稠,散发着泥土的香气。慢慢沉淀,将水分沥出,只留河泥。用布裹起,放于筛下,好玩的工序来了——捶打河泥,一遍一遍,捶打九千九百九十九遍,将泥中空气挤出,直捶打得河泥像最细最细的面筋,摸起来像小孩子的屁股一样光滑,像爱人的肌肤一样绵软。河泥被制成长方体,用油纸裹严,放在阴凉房屋的木箱中,谓之,陈腐。
一年后打开油纸,河泥还是湿润的,散发着时间的味道。再次捶打、揉搓后,开始制胚。用木尺量好,用竹刀割开,放于阴凉处阴干。小孩子好玩泥巴,或许始于女娲补天的基因。如今带着化工味道的橡皮泥不好玩,少了泥土的亲近。
待泥胚接近干透之时,制砚人在灯下已经画好线稿,或画荷莲,或画鱼虫,也有画上人物的,骑于牛背上的牧童、放风筝的小孩,都挺好。将线稿贴在胚上,用刻刀雕胚。清晨,鸡叫声在山谷里传出很远,河水哗哗流淌,制砚人洗了脸,鸡窝里撒过米,扫过院子,用清水冲刷了门前的石板。朝阳已经从山的另一面射进道道红光,晨雾渐小。制砚人开始雕砚,一点一点,雪花一样的泥屑在刻刀下剥落,砚池慢慢显出轮廊。制砚人一遍一遍打磨,目光慈悲,满眼江河,如同看着眼前深爱的女人。
泥胚制好,放于柴炉,点火烧柴,窑口上的烟囱升起青烟。不停火,烧制两天左右,为受热均匀,用河泥将窑口封严,让木柴慢慢燃烧。十日后,开窑,这个急不得,急了,陶砚会开裂。拆开窑口,本来青白的泥胚变得橙红,敲打之下发出钢玉之声。
再一次精细打磨,从二百目砂条,一直磨到两千目。打磨也急不得,慢慢来,陶砚的光泽才会显现出来,玉影般沉静,美人眼眸一样温情如水。呵气则润,自带潮水。
一方古法所制陶砚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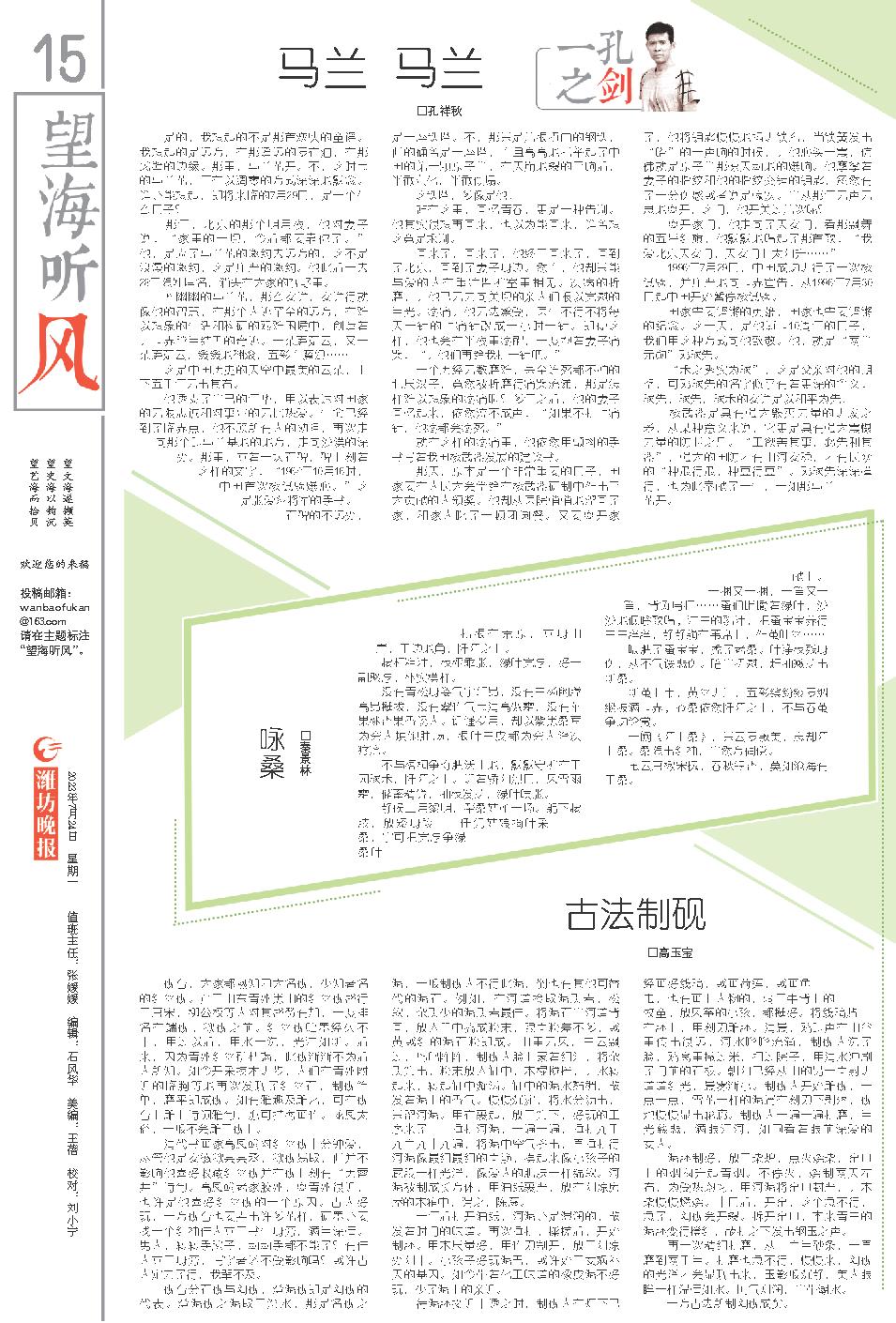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724/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