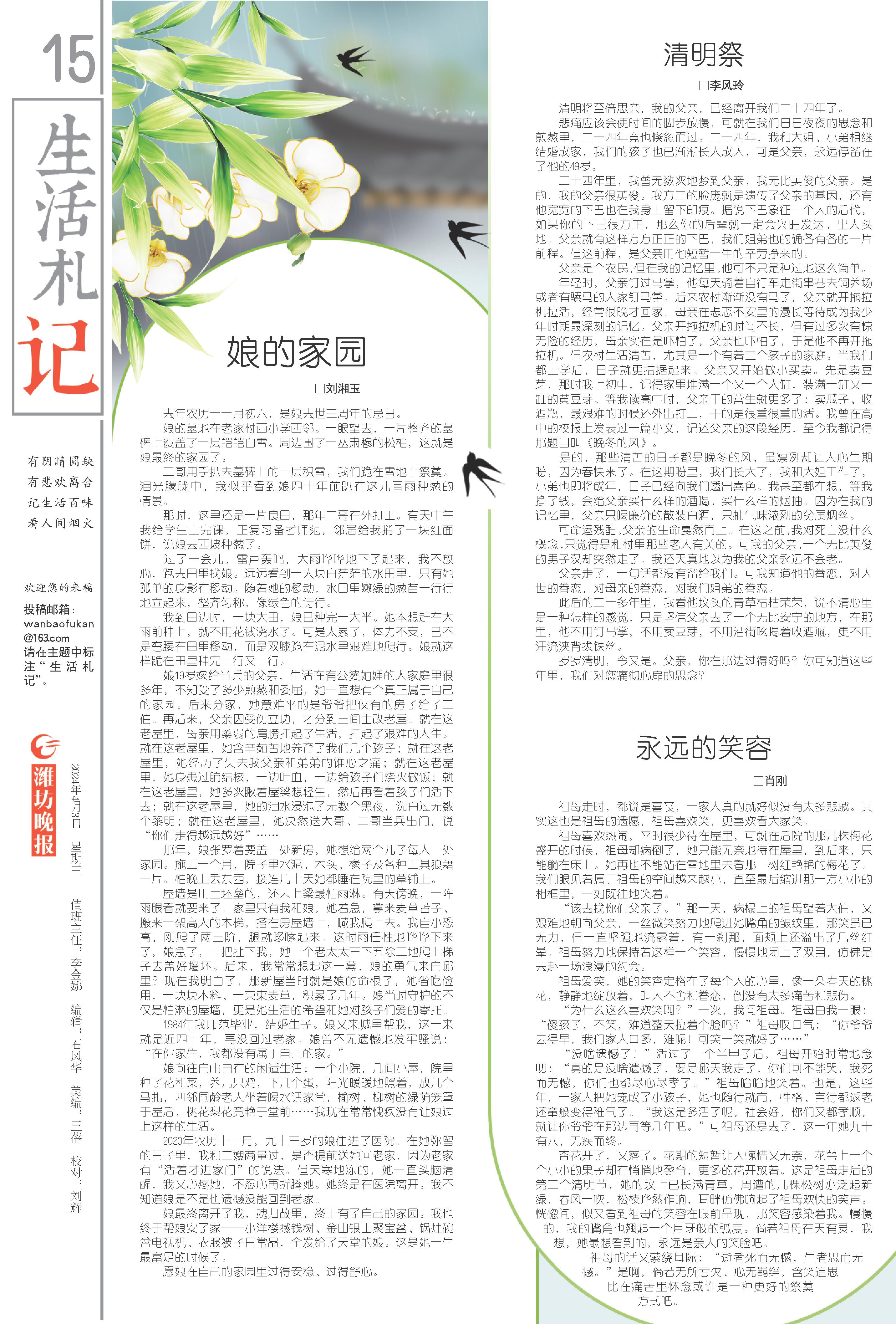01版:导读
01版:导读
- * 郁见春天
 05版:聚焦全市推进高水平开放高质量招商引资暨第四届潍坊发展大会
05版:聚焦全市推进高水平开放高质量招商引资暨第四届潍坊发展大会
- *
将潍坊人的精神品质
融入骨血 - * 情系家乡助环保
- *
墨香融于笔端
书写更好潍坊 - * 逐梦乡村振兴大舞台
 16版:光影记录
16版:光影记录
- * 好好过春天
□刘湘玉
去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是娘去世三周年的忌日。
娘的墓地在老家村西小学西邻。一眼望去,一片整齐的墓碑上覆盖了一层皑皑白雪。周边围了一丛肃穆的松柏,这就是娘最终的家园了。
二哥用手扒去墓碑上的一层积雪,我们跪在雪地上祭奠。泪光朦胧中,我似乎看到娘四十年前趴在这儿冒雨种葱的情景。
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良田,那年二哥在外打工。有天中午我给学生上完课,正复习备考师范,邻居给我捎了一块红面饼,说娘去西坡种葱了。
过了一会儿,雷声轰鸣,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我不放心,跑去田里找娘。远远看到一大块白茫茫的水田里,只有她孤单的身影在移动。随着她的移动,水田里嫩绿的葱苗一行行地立起来,整齐匀称,像绿色的诗行。
我到田边时,一块大田,娘已种完一大半。她本想赶在大雨前种上,就不用花钱浇水了。可是太累了,体力不支,已不是弯腰在田里移动,而是双膝跪在泥水里艰难地爬行。娘就这样跪在田里种完一行又一行。
娘19岁嫁给当兵的父亲,生活在有公婆妯娌的大家庭里很多年,不知受了多少煎熬和委屈,她一直想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后来分家,她意难平的是爷爷把仅有的房子给了二伯。再后来,父亲因受伤立功,才分到三间土改老屋。就在这老屋里,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扛起了艰难的人生。就在这老屋里,她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几个孩子;就在这老屋里,她经历了失去我父亲和弟弟的锥心之痛;就在这老屋里,她身患过肺结核,一边吐血,一边给孩子们烧火做饭;就在这老屋里,她多次瞅着屋梁想轻生,然后再看着孩子们活下去;就在这老屋里,她的泪水浸泡了无数个黑夜,洗白过无数个黎明;就在这老屋里,她决然送大哥、二哥当兵出门,说“你们走得越远越好”……
那年,娘张罗着要盖一处新房,她想给两个儿子每人一处家园。施工一个月,院子里水泥、木头、椽子及各种工具狼藉一片。怕晚上丢东西,接连几十天她都睡在院里的草铺上。
屋墙是用土坯垒的,还未上梁最怕雨淋。有天傍晚,一阵雨眼看就要来了。家里只有我和娘,她着急,拿来麦草苫子、搬来一架高大的木梯,搭在房屋墙上,喊我爬上去。我自小恐高,刚爬了两三阶,腿就哆嗦起来。这时雨任性地哗哗下来了,娘急了,一把扯下我,她一个老太太三下五除二地爬上梯子去盖好墙坯。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一幕,娘的勇气来自哪里?现在我明白了,那新屋当时就是娘的命根子,她省吃俭用,一块块木料、一束束麦草,积累了几年。娘当时守护的不仅是怕淋的屋墙,更是她生活的希望和她对孩子们爱的寄托。
1984年我师范毕业,结婚生子。娘又来城里帮我,这一来就是近四十年,再没回过老家。娘曾不无遗憾地发牢骚说:“在你家住,我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家。”
娘向往自由自在的闲适生活:一个小院,几间小屋,院里种了花和菜,养几只鸡,下几个蛋,阳光暖暖地照着,放几个马扎,四邻同龄老人坐着喝水话家常,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梨花竞艳于堂前……我现在常常愧疚没有让娘过上这样的生活。
2020年农历十一月,九十三岁的娘住进了医院。在她弥留的日子里,我和二嫂商量过,是否提前送她回老家,因为老家有“活着才进家门”的说法。但天寒地冻的,她一直头脑清醒,我又心疼她,不忍心再折腾她。她终是在医院离开。我不知道娘是不是也遗憾没能回到老家。
娘最终离开了我,魂归故里,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我也终于帮娘安了家——小洋楼撼钱树、金山银山聚宝盆、锅灶碗盆电视机、衣服被子日常品,全发给了天堂的娘。这是她一生最富足的时候了。
愿娘在自己的家园里过得安稳、过得舒心。
去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是娘去世三周年的忌日。
娘的墓地在老家村西小学西邻。一眼望去,一片整齐的墓碑上覆盖了一层皑皑白雪。周边围了一丛肃穆的松柏,这就是娘最终的家园了。
二哥用手扒去墓碑上的一层积雪,我们跪在雪地上祭奠。泪光朦胧中,我似乎看到娘四十年前趴在这儿冒雨种葱的情景。
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良田,那年二哥在外打工。有天中午我给学生上完课,正复习备考师范,邻居给我捎了一块红面饼,说娘去西坡种葱了。
过了一会儿,雷声轰鸣,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我不放心,跑去田里找娘。远远看到一大块白茫茫的水田里,只有她孤单的身影在移动。随着她的移动,水田里嫩绿的葱苗一行行地立起来,整齐匀称,像绿色的诗行。
我到田边时,一块大田,娘已种完一大半。她本想赶在大雨前种上,就不用花钱浇水了。可是太累了,体力不支,已不是弯腰在田里移动,而是双膝跪在泥水里艰难地爬行。娘就这样跪在田里种完一行又一行。
娘19岁嫁给当兵的父亲,生活在有公婆妯娌的大家庭里很多年,不知受了多少煎熬和委屈,她一直想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后来分家,她意难平的是爷爷把仅有的房子给了二伯。再后来,父亲因受伤立功,才分到三间土改老屋。就在这老屋里,母亲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扛起了艰难的人生。就在这老屋里,她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几个孩子;就在这老屋里,她经历了失去我父亲和弟弟的锥心之痛;就在这老屋里,她身患过肺结核,一边吐血,一边给孩子们烧火做饭;就在这老屋里,她多次瞅着屋梁想轻生,然后再看着孩子们活下去;就在这老屋里,她的泪水浸泡了无数个黑夜,洗白过无数个黎明;就在这老屋里,她决然送大哥、二哥当兵出门,说“你们走得越远越好”……
那年,娘张罗着要盖一处新房,她想给两个儿子每人一处家园。施工一个月,院子里水泥、木头、椽子及各种工具狼藉一片。怕晚上丢东西,接连几十天她都睡在院里的草铺上。
屋墙是用土坯垒的,还未上梁最怕雨淋。有天傍晚,一阵雨眼看就要来了。家里只有我和娘,她着急,拿来麦草苫子、搬来一架高大的木梯,搭在房屋墙上,喊我爬上去。我自小恐高,刚爬了两三阶,腿就哆嗦起来。这时雨任性地哗哗下来了,娘急了,一把扯下我,她一个老太太三下五除二地爬上梯子去盖好墙坯。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一幕,娘的勇气来自哪里?现在我明白了,那新屋当时就是娘的命根子,她省吃俭用,一块块木料、一束束麦草,积累了几年。娘当时守护的不仅是怕淋的屋墙,更是她生活的希望和她对孩子们爱的寄托。
1984年我师范毕业,结婚生子。娘又来城里帮我,这一来就是近四十年,再没回过老家。娘曾不无遗憾地发牢骚说:“在你家住,我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家。”
娘向往自由自在的闲适生活:一个小院,几间小屋,院里种了花和菜,养几只鸡,下几个蛋,阳光暖暖地照着,放几个马扎,四邻同龄老人坐着喝水话家常,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梨花竞艳于堂前……我现在常常愧疚没有让娘过上这样的生活。
2020年农历十一月,九十三岁的娘住进了医院。在她弥留的日子里,我和二嫂商量过,是否提前送她回老家,因为老家有“活着才进家门”的说法。但天寒地冻的,她一直头脑清醒,我又心疼她,不忍心再折腾她。她终是在医院离开。我不知道娘是不是也遗憾没能回到老家。
娘最终离开了我,魂归故里,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我也终于帮娘安了家——小洋楼撼钱树、金山银山聚宝盆、锅灶碗盆电视机、衣服被子日常品,全发给了天堂的娘。这是她一生最富足的时候了。
愿娘在自己的家园里过得安稳、过得舒心。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08/08-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09/09-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10/10-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11/1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12/1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13/1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14/1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15/1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403/16/Page16-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