堰浯入荆寻踪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民殷国富,成为“五霸之首”,这时期完成了大型水利工程“堰浯入荆”,比闻名世界的都江堰工程早了约400年。该工程位于现安丘东南部的景芝镇,在东古河村与西古河村之间的古浯河河道上筑起堤堰,拦阻流向东北的浯河水,同时开掘6公里长的水渠,接通诸城市石桥子镇都吉台村东北的荆河,引浯水灌溉荆河沿岸的数万余顷稻田。“堰浯入荆”工程对该地区农业发展及水上运输等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奠定了齐国兴盛的基础。
本期撰稿:李存修 王玉芳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可 美编:许茗蕾
校对:曾艳(01、02)王明才(03、04)刘辉(05、06)刘小宁(07、08)
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新闻线索并提出宝贵意见,本周刊邮箱为56352618@qq.com
浯河一年四季水源充足
“堰浯入荆”这项水利工程,位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境内,即现在的安丘市南部景芝镇渠河沿岸部分村庄及诸城市北部的石桥子镇,使渠河沿岸这大片肥沃的土地成为了“巨大的粮仓”。如此浩瀚的水利工程能够顺利实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
使齐国成五霸之首
齐桓公即位后,励精图治,在鲍叔牙、管仲等名臣辅佐之下,齐国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都临淄十分繁华,成为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齐桓公,姜姓,吕氏,名小白,是齐僖公的三儿子,齐国开国之君姜尚第12代孙,公元前685年-前643年执政齐国,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国君。
据《左传》《史记》记载,齐僖公死后,齐国的君位传给其长子齐襄公。齐襄公昏庸无能,为避免无妄之灾,谋士鲍叔牙同公子小白到莒国,管仲和召忽则同公子纠跑到鲁国避难。
襄公十二年(前686),公孙无知杀齐襄公,自立为君。次年,公孙无知被杀,齐国需重立君主。得到消息后,鲁国立即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继位。因怕公子小白回国争夺王位,管仲亲率30乘兵车赶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截击公子小白,果然在莒道(约在今安丘与沂水交界处)遇见公子小白的大队车马。管仲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一箭射去,公子小白口吐鲜血倒下,管仲便返回禀报。其实这一箭射在了公子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公子小白咬破舌尖倒下装死,躲过此劫。
此后,公子小白与鲍叔牙更加警惕,飞速向齐国挺进。最终抢在公子纠之前赶到齐都,顺利登上君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公子纠得知齐桓公即位后气急败坏,派兵进攻齐都。齐桓公派鲍叔牙带兵迎战公子纠,在乾时(今淄博市桓台县)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乾时之战”,大败鲁军,公子纠仓皇退回鲁国。
随后,齐桓公发重兵攻打鲁国。迫使鲁庄公杀掉了公子纠。为国计,齐桓公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摒弃个人恩怨,不仅没杀管仲,还委以重任,拜他为相。
管仲被齐桓公的大度和睿智所折服,从此竭尽全力报效齐桓公。他推行改革,减轻税赋、发展经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齐国逐渐强盛;修建齐长城,抵御外敌,并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终使齐国成为中原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将齐国霸业推至鼎盛。
齐鲁大地上最早的水利工程——“堰浯入荆”就是在此时期诞生的。
太平山为浯水之源 大小水流蜿蜒汇聚
《辞海》称:“浯河,在山东省东部,发源于沂山东麓,东北流经安丘、诸城两县入潍河。”《水经注·潍水》载:“潍水又北径平昌县故城东,荆水注之。水出县南荆山阜,东北流径平昌县故城东。城之东南角有台,台下有井,与荆水通。物坠于井,则取之荆水,昔常有龙出入于其中,故世亦谓之龙台城也。荆水又东北流,注于潍。潍水又北,浯水注之,水出浯山,世谓之巨平山也。”巨平山就是太平山。太平山有两大主峰,第一主峰海拔523米,第二主峰海拔518米,两座山峰由三县拱围。太平山上的雨水,也分别流向安丘、沂水和临朐三县,可谓“一水滴三县”。
北流的太平山之水先进入安丘鲤龙河,后汇入汶河;西去临朐的山水流入了汶河上游;西南山麓临朐县大官庄村的山泉,则是“浯水”距离最远的源头;而来自太平山主峰的水分别从临沂市沂水县圈里乡的上二郎峪和红石峪两村附近山谷流下,沿途接纳了部分细小水流,两水源最终在圈里乡小弓河村南汇入浯河。三个源头相距不过10公里。除此之外,还有大大小小多条细小水流,从大山母体里渗透出来,形成山崖间的小溪,后成水潭,潭水外溢,形成流泉,最终都汇入了浯河。而大官庄村的山泉是浯河的最大源头。一股股细流汇成“堰浯入荆”的母体浯河。
古时安丘位于齐国中南部,地形东西长而南北稍窄,在这片土地上,高高低低起伏着153座山,其中有36座海拔百米以上的山,48条河在其间蜿蜒流淌。
接纳沿途众多河流
浯河全长百余公里
“浯水”就这样从远古走来,弯曲向东流成了浯河。从安丘郚山镇太平山源头到原临浯古河村往东北流经临浯冲积平原经景芝汇入潍河,古老的浯河全长百余公里。
在上游几十公里的流程中,浯河接纳了沿途众多河流,水量变得充沛而富足,才拥有了滔滔不竭的生命力。
在进入安丘界时,浯河接纳的第一条自北向南的支流名为大苑河,全长11.2公里,河道宽阔,流水平稳而清澈。6公里长的中、上游地段,两边均为丘陵,两侧降水量大。这里植被茂盛,风景优美,被称为安丘的“九寨沟”。
第二条为秋峪河,全长8公里,雨量集中。经于家河水库入老子河。
第三条是老子河,全长14.6公里。还有柿子园河、庵子河、孝廉河、水润道河、水廉河、寨庄河、店子河……
此处水流如此密集而丰沛,是因为地处安丘西南部山区,流域内有虎眉山、紫草山、擂鼓山、井子山、双子山、鞍子山、旺山、陈古山、磨山、虎崖、大顶子、大架山、摘月山、摘灯山、城顶山、保国山、八大顶山、钟楼山和太平山等山,海拔百米以上的山有36座。有山就有水,浯河流经了这些山山水水,才成了浯河,直到齐桓公“堰浯入荆”后,又诞生了“渠河”。
再有,在浯河中上游这段密布山水的地带,有个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离此几十公里的西北方,有两道阻挡寒潮冷风的自然屏障,第一道是海拔千米以上的沂山山脉,强硬地阻止了来自大西北的寒流;第二道是绵延耸立的城顶山。地理上的优势使这一地区林木茂盛,雨量充盈,形成一个天然的“大水箱”,供给浯河一年四季充足的水源。
本版图片由孙宝平提供(署名除外)
开渠筑堰实现均衡灌溉
齐国兴建“堰浯入荆”水利工程,一方面大大改善了荆河下游水浇条件,使数万顷粮田得到灌溉,提高了粮食产量;另一方面,减弱了原本丰沛的浯河水流,避免夏季河水暴涨形成水患;同时,又加大了水路漕运地域,便于沿途粮食物资运输,繁荣齐国经济。
古时荆河浯河并行
上游水源流失严重
2600多年前,安丘、诸城一带为齐国属地,在潍河以西、景芝与相州之间,甘泉岭以南,官庄花家岭以东,渠河以南、诸城程戈庄以北的大片地域上,有三条河并流存在。
最北边一条是发源于安丘霹雳山和寒冬山的洪沟河,长45公里,是安丘的第三大河流。洪沟河源头水量丰富,直到今天依然补充着浯河景芝段的水源。中间一条就是浯河,是安丘第二大河流,现在叫渠河。浯河发源于浯山,流经姑幕城(今安丘市石埠子镇)东,东北流经安丘市景芝镇西古河村村东、临浯村前、景芝镇政府驻地西、峡山区王家庄街道大孙孟村注入潍河。
第三条是荆河,发源于诸城市石桥子镇西南方向的荆山,全长接近20公里,流经荆山后、龙石头河、张家岳旺、田家岳旺、吴家沟、高家岳旺、白家岳旺、石桥子、韩家庄、吕家庄子、徐家庄子、大近戈庄、彭戈庄等十几个村庄,最后在都吉台村东北处汇入渠河。因水流较小,当地人叫它小荆河。
许慎《说文》言:“水出灵门(壶)山,世谓之浯汶矣。其水东北迳姑幕县故城东(今安丘市石埠子镇)……浯水又东北迳平昌县故城(今诸城市石桥子镇都吉台村)北,古堨此水,以溢溉田,南注荆水。浯水又东北流,而注于潍水也。”从《水经注》记载可以看出,在古代,荆河和浯河是两条独立入潍的河流。两条河流向大致平行,并不像今天这样,荆河只是渠河的一条支流。
三条河中,流量最充沛的数浯河,其次是洪沟河,两条河流于景芝镇伏留村西南交汇称浯河。从上游下来的水源大多白白流失,且历史上还常造成涝灾。而最南侧的荆河发源于低矮浅丘地区,流程短,流量小,又因流域面积狭窄,水量极为有限,满足不了由此往东南方向的大片粮田的灌溉需求,制约了该地的农业发展。
开凿渠道接通两河 筑起堰坝分浯入荆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记载:浯水堰,《三齐记》曰:“昔者堰浯水南入荆水,灌田数万顷。今尚有余堰,而稻田畦畛存焉。”晋代伏琛《三齐略记》载:“桓公堰浯水南入荆水,灌田数万顷。今尚有余堰及稻田遗畛存焉。”
史书有明确记载,在浯河与荆河之间这片流域,有数万顷土地种植水稻,稻田需要大量水灌溉。在南侧水源紧缺而北侧水源大量流失的情况下,若能通过兴修水利“北水南调”实现均衡灌溉,保障农作物丰产丰收,实为利国利民之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齐桓公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加上宰相管仲的智慧谋略,顺应强国富民的发展需要,经过反复勘探、调研,最终决定在浯河和荆河最接近的地方兴建水利工程,“堰浯水南入荆水,灌田数万顷”。于是,就有了声势浩大的“堰浯入荆”工程。
齐国经勘探发现,浯水与荆水两条河流之间最近之处为6公里,位置在临浯西古河河段至诸城都吉台村北,在这里开凿一条渠道将两河接通。同时,在西古河河段龙湾处东北拐弯的浯河河道上筑起一道堰坝,分流部分浯水通过渠道流入荆河。这条人工开凿的渠道就是“渠河”名称的由来。
“堰浯入荆”建成后,补充了荆河水流,灌溉下游数万顷粮田,增加粮食产量;有效治理浯河水患,兴利除灾。与此同时,该工程也开拓了水路漕运流域,便于粮物运输,从而巩固王权统治。总之,“堰浯入荆”工程的实施,为繁荣当时齐国经济、实现齐桓公霸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堰浯入荆遗迹尚在
彰显古人聪明才智
在景芝镇东古河村、西古河村间渠河北岸有一个叫“龙湾”的地方,残存着一段“堰浯入荆”遗迹。坚固围堰为东西方向,经风剥雨淋、岁月消蚀,至今仍矗立着,似一把巨大的牛梭头。堰长约400米,高出河底五六米,比北岸田地高出2米左右。堤顶高3米左右,最宽处4米多。
环视龙湾四周,走过大堤里外上下,头顶风过树梢的沙沙细语与河底哗啦啦的流水声共鸣,遥想26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人喊马嘶、壮阔热烈的建设工地现场。
景芝镇历史文化研究会党支部书记王玉国是地道的临浯人,和众多临浯人一样,他不仅对浯河有着浓浓的情结,对浯河及其沿岸的人文历史也很有研究。他认为,目前看到的堰其实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为了防止水患在原来的基础上筑起来的,真正“堰浯入荆”的那道古老堰坝还在下面。至于为何筑成牛梭头的形状,据他推断,浯河水量丰沛,齐国的建设者们随着水势,分别从东西两侧缓筑弧形堰坝,以减弱水流冲击,最后逐渐合拢。最终,一道牛梭头形状的堰坝阻挡了原本向东北奔流而去的滔滔浯水,逼部分水流进入新开凿的渠道,形成后来的“渠河”。
“堰浯入荆”工程彰显了齐国水利精英和劳动人民的智慧。难以想象,在那个没有机械、全靠肩挑人抬的年代,齐国究竟耗费了多少财力、多少人力、用时多久才完成如此宏大的水利工程。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单从堰、渠的选址,就体现出古人的聪明才智,令今人叹服。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战事频起。为了竞争生存,各诸侯国纷纷发展经济贸易,增强国力,尤其是齐国,开启农田水利建设之先河,夯实农业基础,换来了物阜粮丰、国富民强,奠定了“五霸之首”的根基。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密集期,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本版图片由孙宝平提供(署名除外)
安丘粮仓临浯历史悠久
浯河是景芝平原四条主要河流之一,也是安丘市境内的第二大河流。因浯河而得名的“临浯”具有悠久的历史。2600多年前的“堰浯入荆”工程使浯河的命运发生变化,而浯河沿岸的临浯因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已成为安丘“粮仓”。
浯河滋润一方土地
临浯段称“运粮河”
“浯河古称浯水,人们在下游开渠灌田,又有上浯(河)下渠(河)之称,今已统称渠河。”《安丘县志》关于浯河的文字记载仅上溯到西汉时期。而齐国的“堰浯入荆”工程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滔滔浯水。
古浯河流经今临朐县蒋峪镇、沂水县圈里乡、富官庄乡,安丘市柘山镇、石埠子镇,诸城市石桥子镇,安丘市官庄镇,进入景芝临浯境内后,流经26个村庄,蜿蜒16公里,在芝泮村西北、伏留村西南方向,接纳了自西向东流来的洪沟河水,经景芝镇区向东北流去。
临浯段浯河当地人习惯称“运粮河”。它从东古河村、西古河村之间拐弯东北、流向西辛庄村南转弯向东,到兆家庄子村北东辛庄村南时又拐弯东北,然后经南林、北林两村之间,高家庄和石家埠两村之间,到苑家庄和西村之间继续东流,经过和平村南、贾岗村北流向东北,过套子村东向东流经院上、周家庄子、班岗三个村子的南边、鞠家庄村北然后向南,绕小河套村西南再向北到尧上东北、刘家庄和西笔墨、中笔墨、东笔墨村南向东南流向仉岗村北,而后又东北流向芝泮村,在村西拐弯向北流向伏留、景芝镇,到峡山区大孙孟一带与潍河汇流进入峡山水库,最终流入渤海。
“堰浯入荆”工程改变了大致平行的浯河和荆河两条河流的命运,原本拐弯流向东北的浯河,因为围堰分流使大部浯河水奔流东去,流经诸城市的都吉台、一溜城阳和相州汇入潍河。久而久之,渠河便成了主河道,形成了“夺荆入潍”的局面,荆河则成为了渠河的一条支流。因此,今天的浯河大部分河段已称渠河,原临浯境内的浯河故道也因水流渐小而慢慢萎缩,最后成为一条枯河,仅从芝泮、伏留段开始到景芝镇、峡山区王家庄街道大孙孟村这一段仍称浯河。这或许就是人们习惯称东古河村、西古河村为“东枯河”“西枯河”的缘故吧。
在上世纪50年代,临浯人在浯河故道又来了一个逆行工程“堰渠入浯”——在西古河村前的古浯水堰上游约400米处渠河上修建了拦河坝,再沿浯河故道修渠,把渠河水又引向浯河故道,灌溉两岸粮田。上世纪80年代,该渠防渗用石头加固,使用并保存至今。
发现200余处古文化遗址 文化堆积深厚
先有浯河后有临浯,临浯与浯河唇齿相依。
关于临浯地名的来历,《安丘县志》记载:临浯村前运粮河是浯河故道,因濒临古浯河,故名临浯,有商、周时期文化遗址。临浯最早是一个村,后来成为乡镇驻地,发展成为建国、和平、西村三个行政村。“临浯”也曾是一个区、一个乡、一个公社、一个镇的代名词。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孙敬明著《潍水集》中《安丘考古述闻》一文说,渠河、浯河、汶河在县境内呈扇形分布,源远流长,最终均汇归于潍水,历经沧桑之变,在这些河流两岸形成了丰富的冲积台地。由于西南面泰沂山脉与北边渤海莱州湾口的交互作用,在此一带形成小的气候环境,空气温润,雨量充沛,是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通过多次的文物普查,在此区域内发现了比较重要的古文化遗址200余处,其中以史前和商周时期的最具学术价值。尤可称道的是,分别在(安丘)县城东南的浯河流域和东北的潍河、汶河交汇处,发现了两处大型遗址群。浯河流域的遗址群以仉岗和芝泮为中心,周围有其他遗址几十处。其中,仉岗尧上遗址、东笔墨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周。2013年,被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遗址大者数万平方米,小者数千平方米,文化堆积深厚,内涵丰富。有的遗址从史前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这些遗址与渠河对面的都吉台遗址、高密柏城镇前冢子头村的史前至汉代各时期遗迹相呼应,说明临浯(浯河)沿岸很早就有人类聚居生存。
临浯土地肥沃水源充足
被誉为三河五岸富饶地
资料记载,安丘解放前,除西朱耿、东古河、西古河3个村属安丘县外,其余30个村属诸城县第二区。1945年划淮安县属甘泉区,1947年建立临浯区,1950年改称潍安县第四区,1952年划为安丘县第十四区,1955年复称临浯区。1958年初撤区建临浯乡,同时将洪沟河以北划出,芝泮以西原属渠河区的村庄划入,同年9月与宋官疃乡合并成立临浯人民公社。1962年4月分为临浯、宋官疃两处人民公社。1984年4月撤销公社建立临浯乡。1994年11月1日,撤乡设镇,面积56平方公里,人口3.4万。辖仉岗、芝泮、东笔墨、中笔墨、西笔墨、刘家庄、尧上、小河套、班岗、鞠家庄、周家庄子、大里岗、小里岗、油坊场、宋家里岗、丁家庄子、院上、套子、北林、东辛庄、西辛庄、南林、西古河、东古河、兆家庄子、小官路、西石埠、东石埠、建国、和平、西村、贾岗、苑家庄、高家庄、东朱耿、西朱耿、石家埠37个行政村。2007年9月,撤销临浯镇,并入景芝镇。
临浯东与景芝镇接壤,西与官庄镇毗邻,北与宋官疃镇以洪沟河为界,甘(泉)花(家岭)公路从境内穿过,乡镇政府驻地临浯,距县城23.5公里。
临浯地处浯河冲积平原,东临潍河,南隔渠河与诸城相望,渠河、浯河、洪沟河从西向东穿流全境,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有安丘“粮仓”之称。素有“要吃干饭,临浯芝泮”的美誉。
当地有句话说得生动——“三河五岸富饶地”。“三河”指的是渠河、浯河和洪沟河,“五岸”指的是浯河两岸、洪沟河两岸和渠河北岸(渠河南岸属诸城),这里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是物阜民丰的好地方。三条河流为当地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临浯曾是安丘县的农业强镇,有过交售爱国粮人均全县第一的光荣历史,有过人均储蓄余额全县第二的排名;临浯人爱国重教,是向国家输送兵员和大中专学生较多的乡镇。
滔滔渠河东去,浯河几近消失,但临浯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还在,临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还在。临浯撤镇并入景芝后,原37个行政村划分为临东社区、临西社区和临北社区,三个社区在发展经济、乡村振兴等方面继续领先,各项工作走在全镇前列。
灾后村庄搬迁河道填平
当地人将临浯境内的浯河叫运粮河,足以说明其漕运的历史功能。今天,虽然运粮河已沉睡在了地下,但轮廓、位置还在。宽阔平坦的河床、那道高2米-3米的原运粮河堤岸在临浯境内清晰可见。人们在河床上耕种、收获,大小村庄散落两岸。
浯河故道挖出白酒
各村名因漕运而生
酒因水而美。景芝酒源于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兴盛于北宋,历史如此悠久,浯水功不可没。“三产灵芝真宝地,一条浯水是酒泉”,一副楹联道出了浯水与景芝酒的渊源。
《山东一轻工业志》载:浯河水质清洌,深处藻萍映绿,浅处水净沙明,游鱼相戏,鹬蚌相争,河畔多生灵芝。汲水烹茶,茶香浓郁;引流酿酒,酒味芬芳。上世纪90年代初,经山东省地矿局分析化验,景芝水(浯河水)里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检验报告称:景芝送检的水质,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被确定为“天然饮用矿泉水”。
据说,上世纪70年代填河造地时,在今景芝镇芝泮村西,浯河拐弯处行船“支牌”码头附近,村民挖出的古船上装有两个大泥坛,内有残存液体,竟然酒味浓郁,想必是行船从景芝装运白酒返回途中在此沉没。
在高家庄村后的“粮湾”码头处同样挖出了古船和桅杆。高家庄村79岁的老支书窦连琪回忆,早年的“粮湾”长约80米、宽约70米,深约3米,“粮湾”是古时运粮河上的一个转运码头。
在临浯,上了岁数的老人都能讲出不少关于运粮河的传说故事。前些年,在石家埠村前、高家庄村后的运粮河北岸,有一种牛蒡的农户在打牛蒡沟时竟打出很多古钱,从唐到宋,其中有徽宗赵佶御书瘦金体的崇宁通宝、崇宁重宝等;还有村民在运粮河捡到锈迹斑斑的宝剑。
就连芝泮、笔墨、河套等村名,也都是由运粮河衍生而来。
芝泮村80岁的赵立南早年一直担任村干部,他说,楚汉战争时期,芝泮村西叫“支派”的小码头,是运送粮食、物品装卸地,大量的运粮船要在该码头支取号牌,类似通行类的凭证,时间久了,为了方便活计,就在那里盖上了房子,繁衍生息。村名先称“支牌”,后演化成“芝畔”“芝泮”。据资料记载,汉代就有“芝盘城”。
小河套村是因为运粮河在此地形成了一个河套而得名;笔墨村的村名也是居住的人在“支派”码头负责执笔记账,是舞文弄墨之人,形成村落后遂取名“笔墨”村,后曾叫民主村,现在分东笔墨、中笔墨和西笔墨3个村。
堰浯入荆惠及两岸 合流后新河称渠河
“堰浯入荆”工程改变了浯河的命运,一条充满活力的“渠河”由此诞生,成为安丘、诸城两地的界河。
上世纪70年代,在浯河上修“大寨田”时,村民在院上村前的古河底挖出一块石碑,上有“浯河”字样,表明古时候浯河是从东古河村、西古河村之间向北,经临浯村东南景芝村西北流入潍河,且水量丰沛,可以通航。
“堰浯入荆”后,浯河水进入荆河,浯河水量远远大于荆河,由于合流后的新河是开渠引水而成,称“渠河”。浯河下游改道且成为“渠河”以后,中、上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叫“浯水”“浯河”。
安丘市石埠子镇召忽墓前有一块“齐召忽墓”碑,是清雍正五年(1727)安丘人马长淑、李文敷、徐天祥和诸城张雯等人所立,碑上有诗为证:“姑幕城西召忽庄,高坟犹在未全荒。生臣业遂雄风有,烈士名留浯水旁……”召忽墓与渠河相距一二公里,而诗中说“烈士名留浯水旁”,而不说“渠河旁”,说明那时还叫“浯水”。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邱锡光(嘉庆六年辛酉科山东乡试解元,诸城人,一说安丘人)所写《游批峡峪记》一文中,说在披甲峪能“南望浯水如匹练”,句中用“浯水”而不是“渠河”。《考古》杂志1963年第10期刊载了山东省博物馆的《山东安丘峒峪、胡峪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其中有一幅遗址位置图,在今天渠河的位置明确标注“大浯河”。
而浯河上游段,特别是今天沂水县境内的那段,至今称为“浯河”。
今天的渠河全长100余公里。从太平山下到景芝古河村,长75公里,属于古浯水河段,占今天全部渠河河段的四分之三,所以,“渠河”可视作古“浯水”。从古河村到诸城石桥子镇都吉台村之间的人工开挖河段,长6公里;从都吉台村到潍河入口处“借用”的古荆水河段,长19公里。尽管这25公里是名副其实的“渠河”,但南岸诸城一些村庄的人们至今仍然习惯叫荆河。
运粮河道填平造地
临浯境内浯河消失
古时的临浯运粮河(浯河),繁忙季节,沿着蜿蜒东进的浯水,船帆浩浩荡荡,往来运输粮食或其他货物。船楫往来,波光帆影,渔火闪烁,满河生机。
今年83岁的张培义从事水利工作37年,从临浯水利站退休。据他介绍,临浯运粮河西起古河,东至伏留,全长16公里,河床宽300米。为防止汛期河水泛滥,上世纪50年代在老河床上开挖了一条子河。1974年一场大水,因部分河道阻塞导致运粮河两岸多个村庄受灾,墙倒屋塌,损失惨重。1976年,临浯公社党委决定根治运粮河:从两岸取土将河床填平造地,再沿河挖一条干渠引水,分流灌溉沿渠农田。
这一年,安丘县委县政府把这一工程列为全县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项目。秋收结束后,公社党委成立领导小组和工程指挥部,下设4个营、16个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组。同时抽调供销社、铁木厂、粮管所、机关、医院、学校精干人员组成了后勤保障组、通讯报道组,打响了“改造运粮河战役”。当时小推车是最先进的工具,但是人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运粮河改造工程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动用人力物力之多,当属临浯农田水利建设史上之最。
那次洪水过后,运粮河的河道被填平造地,临浯境内的浯河就这样完全“消失”。
一条消失了的河流是一段封存于地下的历史文化。国内学术界把消失了的隋唐大运河称为地下文化长廊,那么,临浯的浯河也应该是一条“地下文化走廊”。
浯河沿岸名人志士辈出
浯河历史悠久,沿岸贤人辈出。这里走出了清代被嘉庆皇帝御赐“天下文官祖、一代帝王师”的著名教育泰斗窦光鼐,有民主革命先驱、创建“大同共和国”的刘大同,有北伐时期的革命烈士、早期共产党员刘增等。
窦光鼐不畏权臣
乾隆帝赐诗表彰
窦光鼐字元调,号东臬,诸城西郭家埠人,后随在高家庄教书的父亲迁至高家庄居住。15岁乡试第三名,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历任庶吉士、编修、内阁学士、左副都御史、浙江学政、吏部侍郎、署光禄寺卿、礼部侍郎、左都御史、提督浙江学政、顺天府尹等职。他以其卓然不群的个性,成为一代朝臣典范;他精通经史,与纪晓岚(纪昀)等名流主持文运30年,有《省吾斋诗稿》《省吾斋文集》传世,深得乾隆器重。
窦光鼐为官清廉,忠于职守。任顺天府尹时,惩治奸臣,查处玩忽职守之官吏;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修改不当律例100多条,废寝忘食;代理兵部左侍郎奉命祭南海时,地方官吏竞相送礼,都被他拒绝;任职京师参与秋谳会审,面对刑部众多官员的反对,他坚持原则、量刑定罪。
窦光鼐反对官场黑幕,常常将自己置于险地。任浙江学政时,他上奏举发浙江省仓库亏缺巨大,乾隆帝遂派三名钦差赴浙会同查稽,钦差官官相护,上奏称亏空并不严重,与窦光鼐之奏相悖。乾隆帝又派元老重臣阿桂赴浙再查。阿桂到浙江后也同流合污。至此,窦光鼐既得罪了浙江当地大批官员,又与京城几位钦差大臣形成对峙,但他宁肯“不要性命、不要做官”也不妥协,连夜奔赴平阳县,揪出官员亏空的赃证,贪官得到惩治。
1795年(乾隆六十年),窦光鼐任会试大总裁,因复试贡生涉及对满族弟子的争议被免官,以四品衔告休。同年阴历九月十七卒,归葬于家乡浯河沿岸,墓地就在今景芝镇高家庄村西。
窦光鼐才华满腹,却屡屡因坚持己见、不肯同流合污而遭排挤、打击,展现其做人、为官之风骨。
“两浙山川常毓秀,诸生越旦汝司文。从来士习民成俗,勖彼行知尊所闻。见外发中务清正,涵今茹古去织棼。曰公似矣曰明要,签后纾予一念殷。”这是乾隆皇帝赐给窦光鼐的一首诗,以表彰其清正廉洁不畏权臣之风范。
刘大同响应民主共和 奔走革命40载
刘大同,原名刘建封,号芝叟、风道人,出生于安丘浯河边芝泮村,8岁通诗经、少年中秀才。
光绪二十年(1894),刘建封只身抵达东北。在那里,他结识了宋教仁、廖仲恺等活跃于东北反清浪潮中的仁人志士,并加入兴中会。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任奉吉勘界委员的刘建封奉命勘查长白山及三江之源(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他亲率20余名猛士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用4个月完成勘查任务,完成了《长白山江岗志略》《长白设治兼勘分奉吉界线书》《中韩国境说》《长白山灵迹全影》等著作,绘制了长白山江岗全图,厘清中韩(朝)边界,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担任安图县令时,刘建封提出《筹办边防善后十策》。他从辽宁海龙府移民旗人近百户,又以优厚条件从山东老家移民数百户到安图立业开荒、发展生产。为筹集安图建设急需资金,他不惜变卖老家土地财产。他恤民善政,农林并举,兼兴学商,固边安邦,在任3年,政声卓著。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海龙府(今梅河口)代理知府的刘建封立即响应,在安图竖起义旗,宣告“大同共和国”成立。除了自己更名刘大同外,他还把3个孙子的名字改成了“平民”“平权”“平等”。清廷派兵镇压,刘大同率领义军大胜清军于牡丹岭,后因大批清兵增援,刘大同被迫“南走”。
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刘大同带领同盟会成员携土制炸弹潜入北京刺杀袁世凯未成,后流亡日本。在那里结识了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孙中山对他非常赏识,委任他为东三省支部长。“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大同”,著名诗人臧克家曾这样评价。
日军侵占华北之后,其驻屯军司令官几次请刘大同出山要委以重任,想利用其威望在东北搞“自治”,被刘大同断然拒绝。
出生入死,起起伏伏,奔走革命40年,刘大同被“抄家二次,引渡二次,通缉七次,悬赏逮捕三次,监视二次,驱逐三次,受审十一次,艰险备经屡濒于殆。”晚年,刘大同辗转天津,后定居济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与夫人专程拜访刘大同。感慨万千的刘大同欣然写道:“人人盼共和,徒唤莫奈何。今日新成立,我先击壤歌。”
刘大同在书法、绘画、诗词方面也有较高造诣,徐悲鸿对他十分敬重,两人曾合作《梅石图》,大同画梅,悲鸿补石。刘大同赋诗题画:“藏石不无奇气,塞梅自有铁心。自古画师多少,可逢几个知音?”
1952年,刘大同逝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复原了当年刘建封踏查长白山时所立的石碑3通,在长白山树立了刘大同大型雕像和纪念碑,在安图县松江镇设立了“大同共和国遗址”,以为纪念。
刘增作战英勇顽强
在广州起义中牺牲
刘增,又名刘亦增,1904年生于安丘县临浯乡芝泮村。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刘增经常阅读进步书刊,思想追求进步。
1926年秋,经中共山东省委推荐,刘增和臧克家、曹星海、宋熙来等进步青年一起南下武昌,并考取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改名刘亦增。入校后刻苦学习,各项成绩优异。
1927年,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公然宣布与共产党决裂,武力“清党”,武汉地区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在此时,刘增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刘增战友朱道南回忆: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刘增编入第一大队,后根据斗争形势需要改称为中央独立师,直接参与击败军阀夏斗寅、杨森匪军的战斗,战斗中,刘增担任班长,表现英勇顽强。
1927年6月,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8月,南昌起义爆发后,“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与叶剑英任参谋长的第四军教导团合并,由叶剑英兼任团长,刘增在一连任班长。之后,教导团随叶剑英长途行军,于10月到达广州。经过两个月的休整准备,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由叶挺任总司令、叶剑英担任总指挥的起义队伍打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枪声。战斗中,刘增英勇顽强,始终冲在最前面。在攻占珠江大坝时,不幸被敌人密集的子弹击中,壮烈牺牲,血染江畔。
在景芝镇芝泮村大同公园内,刘增烈士的墓碑赫然伫立。
本版图片由刘浩泉提供
都吉台为平昌故城遗迹
早在龙山文化时期,都吉台就是山东半岛地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该遗址对研究龙山文化、商周遗存及春秋战国时期齐、鲁、莒等诸侯国的势力范围、疆域、文化交流情况,对研究东夷文化及山东半岛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都吉台为贵族斗鸡处
出土大量陶器和铜器
在诸城市区北25公里渠河与荆河汇流处,有一个叫都吉台的村庄,村东有一高台,名曰“斗鸡台”,相传为春秋时鲁国贵族斗鸡的地方,村名因台名谐音而得。
都吉台古遗址南北长103米,东西宽22米,总面积7416平方米,文化层厚8.5米,下层为龙山文化,中层为商周文化遗存,上层有汉代遗物和唐宋遗存,内涵十分丰富。此处出土的大量陶器、铜器证明,早在西周时期,此地便有人烟。
据明万历《诸城县志》记载,斗鸡台在城阳城东北,“高两丈,圆六百步,春秋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季氏与郈氏斗鸡处”。当时的斗鸡多为赌博,各出赌注,以两鸡相斗结果决定输赢。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大夫季孙意如(即季平子)与鲁大夫后恶(即都昭伯)为了取胜,各自都耍了花招。季氏将芥末面洒在鸡翅上,欲以辣坏郈氏鸡眼取胜;郈氏则在鸡爪上暗缚铜钩,欲以利爪斗赢。结果季氏鸡大败,季氏甚为恼火,侵入郈氏之宫地自缢。郈氏联合臧氏到鲁昭公处告季氏,昭公讨伐季氏,季平子请囚请亡皆不许,季氏遂联合叔氏、孟氏三家共伐鲁昭公,鲁昭公败而失国出亡,后恶亦被孟氏所杀。
清咸丰十年(1860),土匪骚扰,民不聊生,斗鸡台已成为较大村庄,有民团,有圩墙,较为安全,因而不少外村人来此避难。民团首领是颇有名气的进士,他组织民团等加固圩墙,增岗设哨,保护难民。由于措施得力,土匪未能骚扰该村,百姓盛传“都吉”“都利”,有口皆碑。后来便改“斗鸡台”为“都吉台”。
早在1979年,该遗址就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都吉台还是救命台。1974年8月13日发生特大水灾,都吉台村东的荆河、村北的渠河河水暴涨,大水过后,全村荡然无存,仅剩大树和屋基没被冲走,1500多名村民躲到台子上避难,无一伤亡。
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都吉台人都重视教育,崇德尚学。从上世纪80年代起,有近百人考入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山东大学等重点院校。
平昌故城文化层重重叠压堆积丰厚
郦道元的《水经注》载:“浯水经平昌城北,城之东有台……名为斗鸡台。”台下有井,传说井内有龙出入,故又曰“龙台”,此井在乾隆十一年(1746)下大雨时坍塌。汉代,斗鸡台所处的地方为平昌侯刘卬封国,即平昌故城。
平昌故城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00米,面积90万平方米,都吉台村就坐落在这座古城遗址上。潍河支流渠河由东向西流经城北,荆河由城南绕经城东,在城东北入渠河。
平昌,汉置县。文帝四年(前176)封齐悼惠王刘肥第八子卬为平昌侯,即此。西汉属琅琊郡,东汉属北海国。三国时,魏置平昌郡于此,后郡废,县属城阳郡。晋复置平昌郡,以县属之。北魏初仍属平昌郡,后改属高密郡。北齐废,入安丘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及省、地(市)文物部门曾对平昌故城址做过多次考查。1982年,诸城市博物馆进行详细调查与勘察,发现故城内的“斗鸡台”及其周围,文化层重重叠压,堆积丰厚,自4500年前的新时器时代龙山文化开始,绵延不断,中无缺环。
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平昌故城东部的斗鸡台上。斗鸡台原来是荆河岸边的一处繁衍生息的台地。新石器时代,人们往往选择台地为居住地点,有利于保存火种,还能躲避水患。台上出土了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石器及蚌器,方唇卷沿的陶鬲应是殷商时期东夷族先民的遗物。西周文化遗迹主要分布于台上及其附近,东周文化遗迹分布于故城的东南部,大大超出了西周时期的范围。
1982年春,在此处挖掘清理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随葬品有铜鼎、盘、壶及部分骨器、蚌器、象牙雕刻、骨贝等,考古专家根据随葬的铜盘上铸有铭文得知,该墓主人即孟姜,此铜盘是姜姓贵族孙叔子为其大女儿出嫁时配送的嫁妆。根据周代“同姓不婚”的制度推知,这时期都吉台一带仍属东夷势力范围。
汉代文化层及遗迹分布于整个故城内,有的地方陶片堆积厚达2米以上,内有板瓦、筒瓦、卷云瓦当等,形体硕大,制作规整,说明这里曾是一座规模宏大、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城邑。故城内曾出土铜焦斗陶瓮、陶盘以及“半两”钱石范等汉代遗物。隋唐以后的遗迹遗物更是遍布故城内外。
传承文化遗产打造新貌
都吉台今成“文化名村”
诸城市石桥子镇都吉台村位于渠河与荆河汇流处,水源丰富,土壤肥沃。全村650户、2240人,耕地面积3700亩。村民以种植绿色蔬菜为主业,生活富裕。该村先后荣获“潍坊市乡村振兴带头村”“省级美丽乡村”等称号。
2019年,诸城市石桥子镇党委政府累计投资500余万元,规划打造了“都吉台”文化村。其设计主要分为村前文体活动广场、台前文化公园、台边商业古街、斗鸡台遗址和文化礼堂展馆五个部分。村前文体活动广场按河边原有地形进行改造,安装了健身器材;台前文化公园有斗鸡图和村里出土文物的浮雕,立在台前的《都吉台的丰碑》详细记述了都吉台的发展历程;透着浓浓古风雅韵的大门楼、仿古商业街则重现了古代都吉台之繁华、厚重的历史。
石桥子镇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打造了都吉台文化礼堂,通过乡情乡知、乡土乡物、乡贤乡风、文化礼堂四个展览和活动场馆,记录并延续着都吉台的前世今生。
如今,都吉台村已成为“文化村”“网红村”。2020年,该村争取库区移民和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资金200余万元,改造提升村容村貌,持续打造“文化名村”。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8888315 13953667072
字画/酒水/礼品回收
空调移机维修回收13573606865
拆除搬家上料装卸15763017881
潍水大战浯河运送物资
在潍水两岸的诸城、安丘、高密段历史上曾有一场著名的战争——潍水之战。汉将韩信率军与楚齐联军于潍水两岸决战,一举消灭了楚国的主力,楚将龙且被杀。潍水之战奠定了楚汉之争的走势。而作为粮食和其他战争所需物资的运输线,临浯运粮河对保障汉军的胜利功不可没。
韩信上游掘坝放水
以少胜多打败楚军
楚汉相争,汉军劣势明显。汉三年(前204)九月,韩信率军东进,攻占齐都临淄。齐王田广败走高密,向楚国求救。项羽派龙且、周兰率20万大军救齐。十一月,楚齐联军在潍水两岸摆下战场,最终,韩信在潍水上游垒坝挡水击破楚军,彻底改变战争局势。
潍河全长250公里,进入峡山后与渠河、浯河三河汇流,形成宽15公里、长20公里的河床,是展开厮杀的巨大战场。龙且、周兰与齐王田广会合入驻高密城(今城阴城故址),并组成齐楚联军在潍河东岸与韩信对峙。当时,有人规劝龙且说:“汉军远离国土,拼死作战,其锋芒锐不可挡。齐楚两军在本乡本土作战,士兵容易逃散,不如深沟高垒,坚守不出。让齐王派他亲信大臣,去安抚已经沦陷的城邑,这些城邑的官吏和百姓知道他们的国王还在,楚军又来援救,一定会反叛汉军。汉军客居两千里之外,齐国城邑的人都纷纷起来反叛他们,那势必得不到粮食,这就可以迫使他们不战而降。”龙且则决意开战。
韩信一面通过运粮河调集粮草,一面下令赶制大批口袋,装满沙土,在潍水上游垒坝堵水。安排守坝士兵听到命令就迅速掘坝放水。
一切准备就绪,韩信率小股人马渡河佯攻,“战败”往回跑,龙且率大队人马过河急追。这时,韩信下令,上游士兵开坝放水,河水汹涌倾泻,龙且的军队一多半还没渡过河去,冲到对岸的也都被突来的洪水吓懵。韩信立即回师猛烈反击,杀死龙且。在潍水东岸尚未渡河的楚军四散逃跑,20万大军瞬间覆灭。
潍水之战韩信大获全胜,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而位于潍河上游、诸城市境内相州镇小古县社区的“韩信坝”也名垂史册。
根据史料记载,韩信坝又称韩王坝,分为:上坝、中坝、下坝。上坝在现小古县村东北;中坝在往北约八九公里的郭家屯镇后凉台村东北侧;下坝位于再往北不远处尚家庄村东南,俗称“北梁子”。
据考证,在“韩信坝”中下坝曾发掘出土了一批戈、矛、铜剑及刺有铜箭头的骷髅等遗物,为“潍水之战”存遗。
潍河西岸留下了诸如大营、小营、营马、料疃许多与军营相关的村名并延续至今。据《史记》载:汉三年冬,韩信在潍水之战中斩楚将龙且,追齐王田广至城阳。时至今日,在古城阳城(今诸城市石桥子镇都吉台村)东约2公里处仍有东城阳、中城阳、西城阳三个自然村。
运粮河为潍水之战提供运输通道
浯河流域面积广、水量大,据说曾通航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上游安丘石埠子一带的河滩上曾挖出铁锚。到了临浯一带,河面宽阔、水流平稳,通航历史悠久。
“堰浯入荆”400余年后的“潍水之战”之所以取得胜利,运粮河的作用不可忽视,韩信调兵遣将,利用浯河(运粮河)运送粮草,保证了潍河两岸战场的物资供应,扭转了战争走势。临浯运粮河也名传至今。
此次战役中,楚将龙且仗着20万大军,以逸待劳,过于轻敌;另外也有地形原因,由于狭长的潍河阻挡,楚军无法发挥人数多的优势,惨遭失败。
潍水之战是一场楚汉双方转折性的战役,此役韩信不仅消灭了项羽的一支有生力量,占领了三齐之地,实现迂回到西楚后方并对其进行战略包围。此战扭转了楚汉之间原来的局势,项羽已经到了完全被动的防御状态,而汉军则进入全面战略大反攻的时刻。临浯这条运粮河则在关键的时间和节点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运粮河经过改造
成临浯第二粮仓
据附近村庄的老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运粮河河道依然存在,河床宽约300米,河底平坦,离地面深约两米,河床中心有条5米-6米宽的小溪流,长年有清水流过。这里还是附近村子里的孩子们割草放牛、剜菜、捞鱼的乐园。
2022年至2023年间,笔者一行曾连续五次对浯河临浯段进行地质地理考察,走访了沿河村庄多位老人,对运粮河的认识一次比一次清晰:不论是在高家庄村后的“粮湾”,还是芝泮村后的沉船,还有那些至今仍深埋在河道土层里的桅杆、铁锚、船板等等,是当年改造运粮河时人们曾亲眼见过的实物。只可惜当时的人们保护意识不强,受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制约,更没有深入挖掘和保护,那些出土的物品很快就被毁掉了。但这一切却能够充分证明运粮河曾经的辉煌。
治理后的运粮河,从东古河村、西古河村之间的龙湾到伏留水库上游,原先宽阔的河床全部变成了平坦、肥沃的高产田,成为临浯的第二粮仓。运粮河由此真正成了一条沉睡在地下的河流。但是,直到今天,细心的人们仍可以看到,沿途1米左右高的河岸在两边时隐时现,比粮田明显高出一截,时刻提醒着人们运粮河的曾经。
今天,这里虽不再有“渔歌互答”和“灯影明灭”的繁华景观,但它用沉甸甸的粮食和有机果蔬回报两岸的人们,丰富了菜篮子,鼓了钱袋子,让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越来越美好。
本版图片由王玉芳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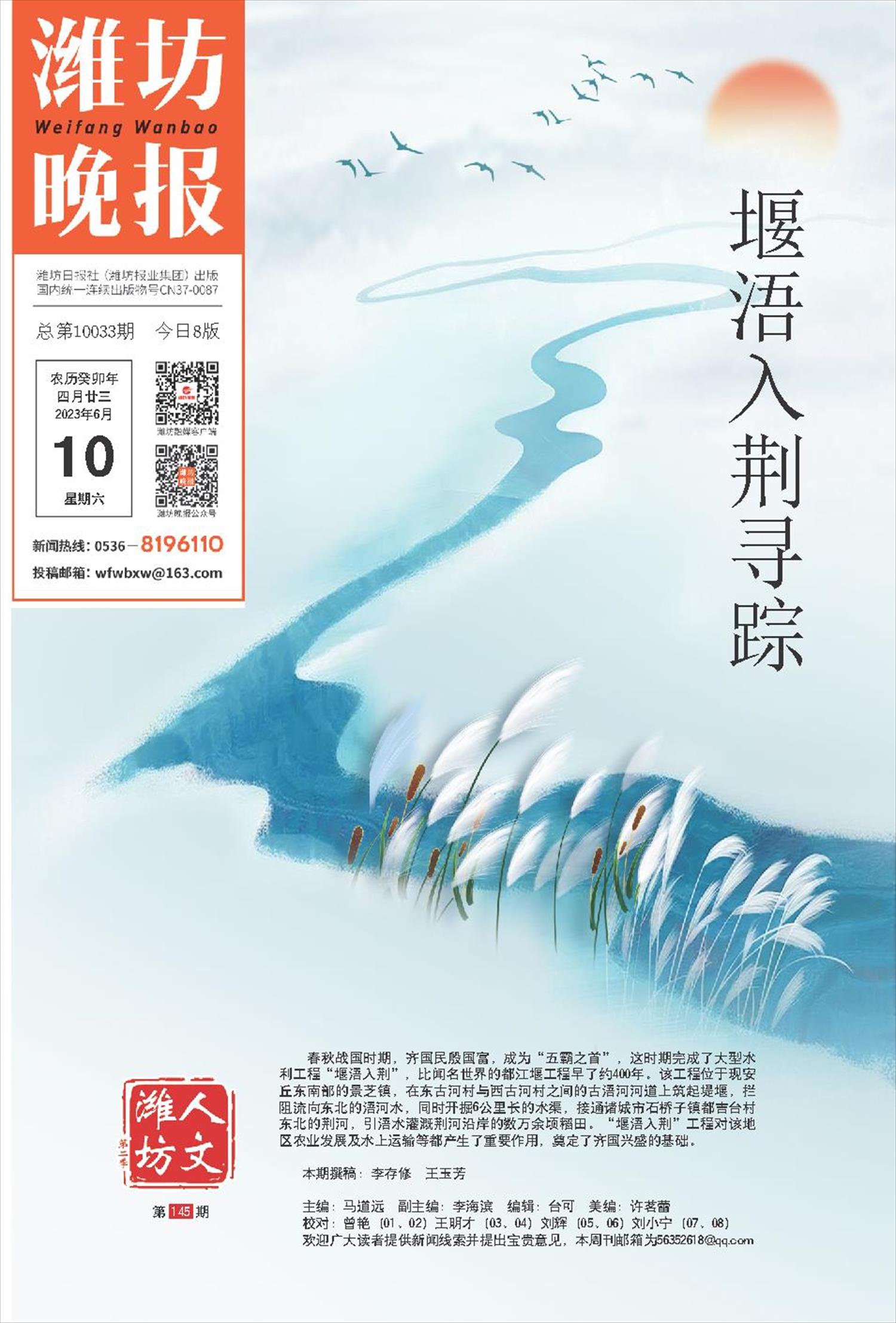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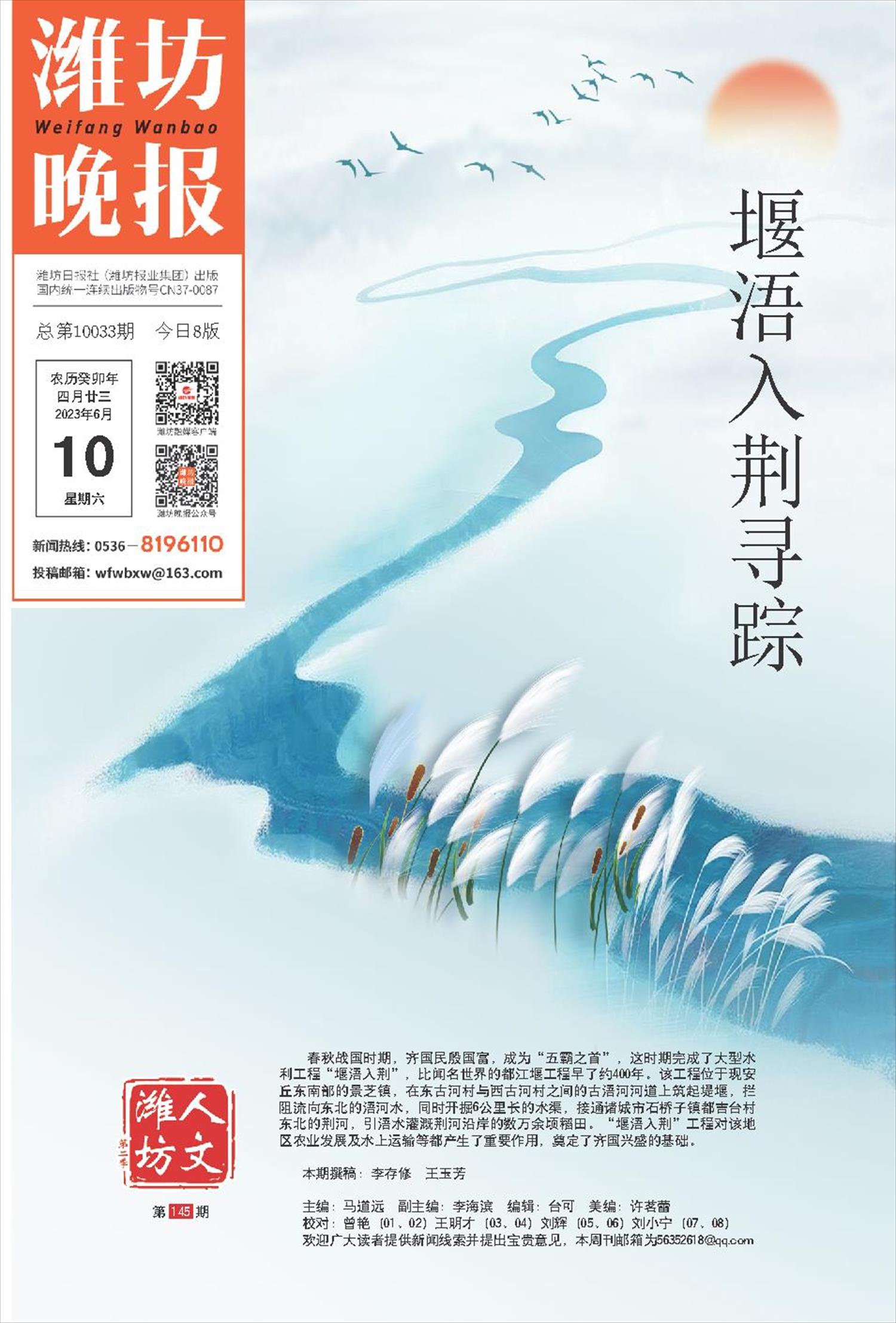







 01版:堰浯入荆寻踪
01版:堰浯入荆寻踪
 07版:堰浯入荆寻踪
07版:堰浯入荆寻踪